專題企劃/國際人權公約在臺灣
廖浩翔|本刊助理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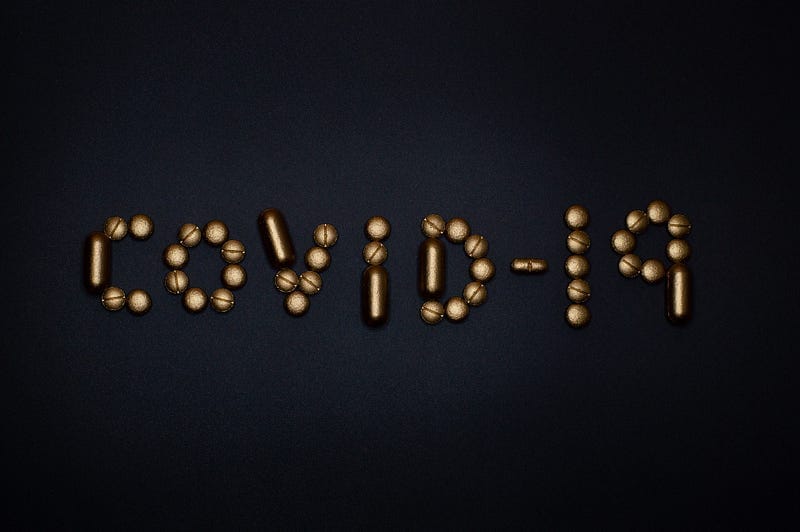
疫情之下的您,生活還安好嗎?或許,多數讀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疫情之下,困難的不只是配合各式防疫限制,像是戴上口罩,外帶餐點而 不再內用等等;還有認清過去的生活模式已成過去,我們得在一片混沌陌 生中,找到一絲還能依循的生活 / 生存軌道。 或許,有些人順利或勉強調適,另一些人則落入困境中掙扎求生。雖然病 毒不會挑人,但疫情帶來的衝擊,並不是均值的;政府或社會在疫情中的 應對,其實加遽特定群體的生活困境。也就是,病毒其實讓各國社會既有 的不平等,以戲劇化的態勢暴露在我們面前。
隱形於疫情之下的哭泣:兒童
雖然確診案例中,兒童不是主要組成部分,兒童受到的衝擊卻往往在討論中 被隱形。首先,學校停課,便衝擊兒童的教育權。截至 2020 年 4 月,全球共有 188 個國家關閉校園,影響超過 15 億名兒少。儘管大部分國家改用遠距教學, 卻有高達 7 成的低收入國家沒有實施 ( 或許是沒有能力,或沒有足夠資源 ),且 在疫情前,全球已有高達 1/3 的兒童,無法取得數位網路資源 (UN, 2020a, pp. 7–8);這些兒少不僅因此停課,也停學了。就算在臺灣,也有許多家庭需要多位 孩子擠在一台螢幕前。其影響不容小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¹ (2021) 即發現,因 為疫情,全球缺乏基礎閱讀能力的兒童,正急速增加²。而對於本就非常仰賴面 對面的互動與支持的身心障礙學生而言,遠距教學使其比其他學生,學習成效打 了更多折扣 (UN, 2020a, p. 12; Melissa et al., 2020, pp. 38–39)³。
[1]該組織全稱原文為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簡稱 UNESCO。
[2]疫情爆發以前,全球缺乏基礎閱讀能力的兒童已在下滑,預計 2020 年將能從 4.83 億降低至 4.6 億名兒童,疫情下的實情,卻是急速增長至 5.83 億 (UNESCO, 2021)。
[3]之所以如此,蘭雅國中林思賢老師 (2020) 舉例解釋,障礙兒童多元的限制與需求,往往 讓他們困難於使用線上學習平台。例如,學生可能無法自行讀懂課程內容,或需要老師即 時互動,來協助學生保持專注。而受疫情影響心理狀態的學生 ( 如:仰賴穩定與規律的自 閉生 ),也需要老師及時的支持與等待。雖然線上學習平台有許多師生即時互動的功能, 卻遠不及於面對面般具體真實。此外,學校平時也為學生擔負或媒合了許多支持服務 ( 如: 提供輔具、助理員協助、物理治療師、家庭支援等 ),確保障礙生能無礙開展校園生活。 障礙生這方面的需求,不會因為停課而消失。如何在疫情期間維繫支持,又能合乎防疫規 定,無疑是艱鉅的挑戰。
當政府鼓勵 / 強迫民眾待在家中,關閉學校等其他公共設施與服務,大部分孩 子或許 「 只是 」 暫時失去了學習與遊樂的地方,但對有些孩子來說,學校原本是他 們的避風港,這種回應疫情的方式,卻將他們無情掃入暴力的烽火。世界各國的家 暴通報率都在上升 (Melissa et al., 2020, p. 41; UN Women, 2020a)⁴。疫情帶給家長 的焦慮,增加了暴躁衝突的可能,在緊密又無法避開的相處下,孩童可能因此成了 出氣包。就如一位奈及利亞 13 歲女童的心聲,「( 疫情帶來的 ) 經濟狀況和就業的 不穩定性,讓他們 ( 指父母 ) 變得很容易生氣,讓待在家變得更困難。去到學校和 同學相處,是曾經存在的一種逃離方式 」(Melissa et al., 2020, p. 29)。 當學校關閉,甚至封城,孩子不僅無法逃離,老師或社工也不再能透過觀察孩 子身上有無傷勢,以協助孩子求助。疫情創造了完美的受暴環境,而孩子困在其中。 不過,並非每一位孩童都受到一樣的暴力威脅,身心障礙、女童、難民與其他弱勢 兒童,有更高的受暴比例,卻陷在更艱難的求助困境 (UN, 2020a, p. 10; Melissa et al., 2020, pp. 41–43; UN Women, 2020b, p. 11)。
[4]根據聯合國婦女署 (2020a) 的統計,疫情爆發前,全球已有高達 2.43 億 15 至 49 歲的女性受 到來自伴侶的暴力,甚至超過三分之一被謀殺的女性,加害者為前任或現任伴侶。政府因疫情 祭出封城措施後,各國都接獲更多家暴求助電話 / 訊息。舉例而言,法國、塞浦路斯、新加坡接 到了比平常多三成的求助電話或家暴舉發。
當學校關閉,甚至封城,孩子不僅無法逃離,老師或社工也不再能透過觀察孩 子身上有無傷勢,以協助孩子求助。疫情創造了完美的受暴環境,而孩子困在其中。 不過,並非每一位孩童都受到一樣的暴力威脅,身心障礙、女童、難民與其他弱勢 兒童,有更高的受暴比例,卻陷在更艱難的求助困境 (UN, 2020a, p. 10; Melissa et al., 2020, pp. 41–43; UN Women, 2020b, p. 11)。
瘟疫與性別的交織:婦女與女童
學校停課後,大眾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是:「 誰來照顧孩子? 」 誰來替他們安裝視 訊設備,與老師協調遠距教學的事宜?孩子肚子餓了,是誰會主動到廚房趕緊弄點 吃的?孩子遇到困難時,通常第一個會叫喊誰?
媽媽。或許讀者不用仔細思考,也能得出這答案。
既有研究已告訴我們,女性承擔了比男性更多的親職勞動 (Hochschild, 1989/2017),而全球平均而言,疫情讓女性比男性多負擔了 3 倍的親職照顧工作, 使更多女性深陷親職照顧與工作之間的拔河。這些照顧工作不只是育兒,還包括照 顧長者與患病的親人 (UN, 2020b, pp. 13–14)。於是,許多女性 ( 尤其是無法遠距工 作的女性)必須抉擇,該保有工作與穩定收入,還是放棄工作。既有研究也告訴我們, 當夫妻兩人中有一人必須放棄工作,放棄的幾乎是女人,尤其社會上多數女性所從 事的工作薪水比較低廉 (ILO, 2018)⁵,而合理化了這個實際上並不正義的抉擇。
[5]根據國際勞工組織 (2018) 的全球性研究,女性的月薪不及男性的八成。也就是,女性每個月的 收入比男性少了至少 20%,但是當聚焦在開發中國家,兩性間的薪資差距其實更大。促成如此 「 性別工資差異 」(gender pay gap) 的因素很多,包括:同工不同酬、傳統上由女性從事的職業 薪水較低 ( 如:清潔員、秘書、護士等 )、女性被要求擔起親職責任而無法完全投入職場或只能 從事兼職零工。
問題不僅如此。由於女性的收入普遍較男性少,疫情對女性與單親媽媽的經 濟衝擊更為劇烈。譬如,開發中國家有高達 7 成的女性,靠著沒有就業保障的地下 經濟⁶度日,像是家務清潔、打零工、攤販,她們必須每天工作才能糊口,但疫情 之下,多數的她們將失去工作 (UN, 2020b, pp. 4–5)。聯合國婦女署⁷ (2020b) 預 估,疫情將造成約 2.47 億位 15 歲以上的女性陷入極度貧窮⁸ ,比同齡男性整整多 了一千萬人 (p. 7)。
[6]原文為 informal economy,又譯 「 非正式經濟 」。
[7]全稱為聯合國促進性別平等與賦權女性署 (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簡稱聯合國婦女署 (UN Women)。
[8]亦即一天只能消費少於 1.9 美元 ( 約臺幣 53 元 )。
除了母親,疫情期間親職照顧工作落在女孩 ( 而非男孩 ) 身上,也是全球皆然 的現象。根據調查,每 5 位女孩中,即有一位表示需要負擔太多家事,而阻礙在家 學習 (Melissa et al., 2020, p. 39)。當家庭失去收入,待在家中的女孩往往被要求 撐起家計,投入險惡的勞動環境,甚至因此被迫未成年結婚,或從事性交易,來為 家裡賺取收入。她們於是暴露在剝削、性病、性別暴力與意外懷孕的風險,相比同 齡男孩,她們更可能因此永遠無法再回到學校,從此停學、失學 (Akmal, Hares, & O’Donnell, 2020)。
強化阻礙的高牆:障礙者
因應疫情,政府要求人民戴起口罩、維持社交距離、待在家中、封城等,這類 防疫政策其實預設了 「 每一個人 」 都能配合規定並維持基本生存。實際上,這些 預設並未將障礙者納入考量。譬如口罩的設計、取得與配戴方式,其實對不同障礙 者,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阻礙:小耳症患者因耳朵構造,無法順利配戴一般醫療口罩;有些腦麻患者則可能因流口水,無法保持口罩乾燥,影響防護功能;需要閱讀唇語 的聾人,則因為大眾以口罩將嘴形罩了起來,而無法順利溝通 ( 人約盟,2020)。 當口罩已經成了公共交通與公共場所的通行證,無法順利適應口罩的障礙者,不 就變相被排除於社會之外?
以遠距教學替代實體教學,其實也預設每位回到家裡的孩子,都有能無時無 刻照顧他們的家長。然而,同步並行的防疫措施,卻沒有撐住為人父母的障礙者。 Lamagdeleine(2021) 報導中的愛文斯 (Crystal Evans) 是位育有 1 女的單親母 親,因為患有神經肌肉疾病而行動不便。她本可以邊在家工作,邊照顧女兒。但 在疫情之時,一切卻變得困難重重,廚房更是成了近在眼前卻無法到達之地。因 為乘著輪椅的她,需要藉助助理員才能使用充滿阻礙的廚房,但防疫政策的限制, 讓她申請不到助理員來家中⁹。 獨立擔起親職責任,對障礙者而言,竟是奢侈,在 疫情面前更是。
[9]障礙者其實很難找到完全合格、行動方便自在的住居環境,因為無障礙環境合格的房屋,其實 渺渺無幾。於是,疫情期間,她曾要求保險公司,給付改善無障礙環境的費用。但是,保險公司 屢次拒絕,認定有助理員協助,足以讓她過著基本生活。實情是,疫情之下,她找不到助理員, 只能勉強忍著不方便度日。
身體損傷並不是造成障礙者生活不便的唯一因素,沒有考量障礙者需求的社 會環境,更是關鍵。誠如電臺主持人余秀芷榮獲金鐘獎時所言:「沒有障礙的人, 只有障礙的環境」¹⁰。不過,從上述例子卻能看見,社會的集體想像中並不存在障 礙者,政府所祭出的防疫政策,是以「一般人 / 健全人」為標準,忽略了障礙者 的生活處境,將阻礙的高牆築得更高、更厚實;以學術名詞而論,這是健全主義 (ableism) 的壓迫 (Yoshida et al., 2021)。
[10]障礙者普遍會遇見的日常不便,請參閱聯合報鳴人堂葉靜倫 2019 年的〈出門就是找麻煩?沒有 障礙的人,只有障礙的環境〉一文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0626/4109997)。
健全主義的結果,輕則造成障礙者的不便與社會排除,重則導致障礙者成為疫 情下,曝於險境的群體,不僅更容易染疫,染疫後也容易發展為重症 (UN, 2020c)。 以英國為例,疫情下重度障礙者的平均死亡率,竟為健全人的 3 倍,輕度障礙者則 約為兩倍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2021)。¹¹有學者認為,因為歧視與刻板印 象,讓障礙者平時即難以獲得醫療保險的保障,就算就醫,醫療體制中既存的各種 不友善,也時常無法滿足障礙者的醫療需求;這類種種 「 健康不平等 」 的情形,使 其染疫時容易發展為致命的重症 (Sabatello et al., 2020)。
[11]男性與女性障礙者間的死亡率其實有些許差異。男性重度障礙者的死亡率為健全男性的 3.1 倍, 輕度男性障礙者則為 1.9 倍;女性重度障礙者的死亡率則為健全女性的 3.5 倍,輕度障礙女性 為2倍。其中,學習障礙者 (learning disability) 的死亡率更高,為健全人的 3.7 倍。
但如此駭人的事實,不單源於障礙者的健康狀況,政府所要求的防疫措施與 提供防疫資訊的方式,也可能加劇障礙者的困境¹²。 例如依賴他人協助方能穿越 馬路的視覺障礙者,可能因此無法出門採購,遑論染疫時自行赴醫院就醫。失控 的疫情也意味著,醫院的軟硬體將大幅更動,而可能阻礙需要就醫的障礙者:非 緊急的醫療照護服務可能停擺,將嚴重衝擊仰賴長期醫療照護的障礙者;因應疫 情緊急騰出的負壓病房,也因缺乏無障礙設計或沒有提供輔具,而無法給障礙者 使用。此外,政府提供防疫資訊時,雖然有手語翻譯,卻沒有其他的溝通形式 ( 如:點字、易讀版 ),播報人員若全程戴上口罩,可能讓不熟悉手語與複雜句型, 或是需要閱讀唇語的障礙者,無法順利獲得防疫資訊 ( 人約盟,2020; UN, 2020c, p. 5)。甚至,部分國家分配醫療資源的決定,隱含對障礙者 「 生命價值 」 的歧視性預期,使障礙者恐因此被排除於醫療資源之外 (UN, 2020c, p. 6) ¹³,落 入染疫卻無人治的風險中。
[12]事實上,目前仍無法斷定障礙者染疫風險較高的原因。障礙者長期形同 「 隱形公民 」,許多關於 疫情的研究,並未聚焦障礙者的處境,因此僅能從過去經驗與現況推敲 (Sabatello, Landes, & McDonald, 2020)。
[1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因爲無法生活於充滿障礙的社會環境,而 「 困在 」 照護機構內的障礙 者,由於難以維持社交距離,容易 「 被成為 」 防疫破口,暴露於感染的風險 (UN, 2020c, p.5)。 疫情帶給障礙者的困境無法以一兩段敘述完整,詳細情形,可以參閱黃榆婷 2020 年於《 多多 益善 》撰稿之〈【人權星期三】疫情中的隔離障礙:戴不了口罩、在輪椅上過夜、收不到防疫 資訊、在全景監控中如廁更衣〉(https://rightplus.org/2020/05/06/cwt-wednesday-7/),以 及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2020 年出版之《2020 兩公約平行報告》第 8 頁至第 10 頁 (https:// covenantswatch.org.tw/wp-content/uploads/2015/12/CW_2020-parellel-report-on-ICCPRand-ICESCR_online_CH_REV.1.pdf)。
社會不平等所造就的不均值傷害,需要 「 人權疫苗 」 來療癒
當然,各國政府的防疫政策,是緊急狀況下的不得不。不過,我們不能忽視防 疫所帶來的非預期後果,尤其這些後果,多數是可以避免的⸺因為它們並不來自 病毒本身,而是源自不平等的社會處境;病毒只是揭發並撕扯了這瘡疤。
防疫的各項政策與限制,預設了每一個人都能在保持社交距離、不與他人接 觸、戴上口罩等,保持基本的生存;停學的孩子,回到家可以藉由網路的影像與聲 音上課,並有大人的悉心照料;每一個人,當有症狀,也能享有相同品質的醫療服 務……但是,這一切都不是目前社會的實際情況,疫情前就已經不是。
不平等的社會處境,讓不同群體,站在不同的位置上適應疫情下的生活,也因 此遇見不同程度的傷害。無法反抗強制力的兒童被關在家中,成了家暴的高風險群。 因為性別刻板印象,相較男童,女童較容易被要求擔起家計與家務勞動,受到童婚 與性剝削的威脅,最後輟學;女人除了拔河於家務與職涯,在貧窮國家中,則多參 與非正式工作,而較男人容易陷入極度貧窮。障礙者則因為社會環境既有的阻礙, 在疫情下掙扎於生存邊緣。但,這些只是冰山一角。當我們看向階級、族群、難民、 移工、無家者等多元身分,傷害其實更為多元交織。
不過,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巴切萊特 (Michele Bachelet) 提醒,我們其實有「人 權疫苗」,也只有這一劑,能夠癒合疫情所加劇的社會撕裂 (Bachelet, 2020)。它 以《世界人權宣言》為主要成分,各國藉由簽署並實踐各部國際人權公約,來施打 這疫苗。它們不只要求政府 「 不能做什麼 」,如尊重人民的公民自由,更要求政府 「 敬謹從事地多做什麼 」,尤其矯正社會不平等,提升弱勢群體地位,並賦予他們足夠力量,自立生存於社會,倡議發生在自己 / 他人身上的不義。從《兩公約》¹⁴ 訂定 生而為人的各式權利,到其他部關注特定群體的人權公約¹⁵,70 多年來聯合國發展 了鉅細彌遺的指引與監督機制,一步一步引導各國形塑務實可行的長期行動計畫與 資源分配,讓 「 人權 」 不再只是理想,而是能夠落實的政策工具。事實上,本文所 描述的兒童脆弱處境、性別不平等,以及障礙者因為社會環境阻礙而遇見的困境, 原本即是各部人權公約的守備範圍。
[14]為《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合稱。
[15]《兩公約》以前,為回應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種族屠殺、種族滅絕事件,聯合國 1965 年通過《消 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兩公約》通過後,則陸續研擬並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1979)、《禁止酷刑和其他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1984)、 《兒童權利公約》(1989)、《保護所有移工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1990)、《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2006) 與《保護所有人免於強迫失蹤國際公約》(2006)。
疫情之下,我們見證社會不平等的威脅。單以現金紓困,無法從根本解套,更 是誤解不平等的本質。我們其實有機會趁這波疫情,細緻了解它所凸顯的社會不平 等,並以人權為基礎,理出改善的行動計畫,建立更為強韌且包容的社會。然而, 願不願意理會這警鐘,端看各國政府的抉擇了。
參考文獻
-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 人約盟 ]( 主編 )(2020)。2020 兩公約平行報告。https://covenantswatch.org.tw/ wp-content/uploads/2015/12/CW_2020-parellel-report-on-ICCPR-and-ICESCR_online_CH_REV.1.pdf
- 林思賢 (2020 年 3 月 23 日 )。面對武漢肺炎,校園中的 「 特殊學生 」 比其他同學承受更大壓力。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2810
- Acosta, A. M., & Evans, D. (Oct. 2, 2020). COVID-19 and girls’education: What we know so far and what we expect.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https://www.cgdev.org/blog/covid-19-and-girlseducation-what-we-know-so-far-and-what-we-expect-happen
- Akmal, M., Hares, S., & O’Donnell, M. (2020). Gendered impacts of covid-19 school closures: Insights from frontline organizations.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https://www.cgdev.org/sites/default/ files/gendered-impacts-covid-19-school-closures-insights-frontline-organizations.pdf
- Bachelet, M. (December 10, 2020). Statement by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Michele Bachelet for Human Rights Day 10 December 2020. 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Human-rights-key-to-build-theworld-we-want.aspx
- Chen, B., & McNamara, D. M. (2020).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medical rationing and COVID-19. Asian Bioethics Review, 12(4), 511–518. DOI: 10.1007/s41649–020–00147-x
-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PRD]. (2018). General comment no. 6 (2018) on 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8/119/05/ PDF/G1811905.pdf?OpenElement
- Gleason, J., Ross, W., Fossi, A., Blonsky, H., Tobias, J., & Stephens, M. (March 5, 2021). The devastating impact of covid-19 on individual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JM Catalyst Innovations in Care Delivery. https://catalyst.nejm.org/doi/full/10.1056/CAT.21.0051
Hochschild, A. R.(2017)。第二輪班:那些性別革命尚未完成的事 ( 張正霖譯 )。群學。( 原著出版於 1989 年 )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2018). Global wage report 2018/19: What lies behind gender pay gaps.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 dcomm/ — -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50553.pdf
- Lamagdeleine, I. S. (April 26, 2021). For physically disabled parents, Covid’s trails are amplified. Undark. https://undark.org/2021/04/26/physically-disabled-parents-navigating-covid-19/
- Melisa, B., Sulaiman, M., Arlini, S. M., Qaiser, M. H., Thiyagarajah, S., Dulieu, N., Orlassino, C., Loperfido, L., Ritz, D., O’Hare, G., Gordon, M., Mepani, B., van Beers, H., Omoni, A., Rees-Thomas, P., Siddiqui, S. A. Arafat, Y., Orsander, M., Mendoza, P., … Clacherty, J. (2020).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Children’s Rights: A global research series. Save the Children. https://resourcecentre.savethechildren.net/ node/18174/pdf/the_hidden_impact_of_covid-19_on_child_rights.pdf
-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February 11, 2021). Updated estimates of coronavirus (COVID-19) related deaths by disability status, England: 24 January to 20 November 2020. https://www.ons. gov.uk/peoplepopulationandcommunity/birthsdeathsandmarriages/deaths/articles/coronaviruscovid19relateddeathsbydisabilitystatusenglandandwales/24januaryto20november2020
- Sabatello, M., Landes, S. D., & McDonald, K. E. (2020).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COVID-19: Fixing our priori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 20(7), 187–190. DOI: 10.1080/15265161.2020.1779396
- United Nations [UN]. (2020a). Policy brief: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children.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4/160420_Covid_Children_Policy_Brief.pdf
- United Nations [UN]. (2020b). Policy brief: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women.https://asiapacific.unwomen.org/-/media/headquarters/attachments/sections/library/publications/2020/policybrief-the-impact-of-covid-19-on-women-en.pdf?la=en&vs=1406
- United Nations [UN]. (2020c). Policy brief: A disability-inclusive response to COVID-19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on_persons_with_disabilities_final.pdf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21). Pandemic-related disruptions to schooling and impacts on learning proficiency indicators: A focus on the early grades. http://uis.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vid-19_interruptions_to_ learning_-_final.pdf
- 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UN Women]. (2020a). COVID-19 and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https://www.unwomen.org/-/media/ headquarters/attachments/sections/library/publications/2020/issue-brief-covid-19-and-endingviolence-against-women-and-girls-en.pdf
- 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UN Women]. (2020b). From insight to action: Gender equality in the wake of COVID-19. https://www.unwomen.org/-/ media/headquarters/attachments/sections/library/publications/2020/gender-equality-in-thewake-of-covid-19-en.pdf?la=en&vs=5142
- Yoshida, K. K., Schormans, A. F., Niles, C., & Mahipaul, S. (April 25, 2021). CANADA: How COVID-19 amplifies the complexity of disability and race? The Conversation. https://theconversation.com/ covid-19-amplifies-the-complexity-of-disability-and-race-157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