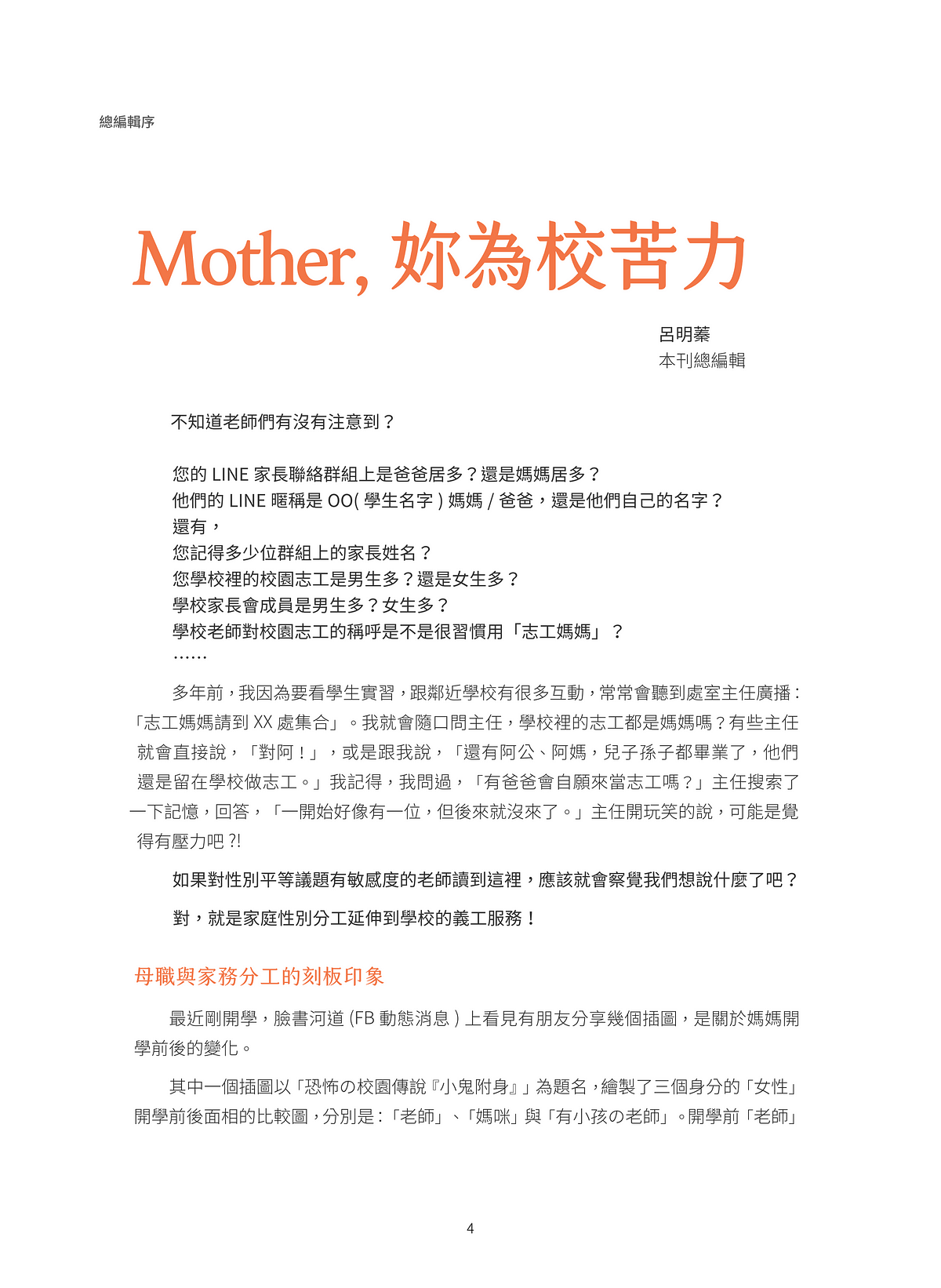Her Stories
雷文玫|陽明大學醫學系公共衛生暨醫學人文學科副教授
觀察母職:我的母親
我希望有一天,母親節是屬於所有照顧者的節日,而不只是某一個女性;我希望母親們即使有孩子,也不必很堅強地犧牲奉獻,仍然能夠擇其所愛,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自己。
會這麼想,跟我的母親有關。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當母親是一個很辛苦,但很了不起的工作。因為我的哥哥有重度腦性麻痺,當別的母親會隨著小孩的成長而喜悅,並且能夠逐漸放下擔子,我哥哥連最基本的吃飯、睡覺、走路等等,一輩子都需要別人幫忙,頂多只能避免惡化。儘管如此,媽媽總是強悍地捍衛著哥哥的利益,確保他吃得好、睡得好,假日還會帶喜歡外出的他開車或搭捷運兜風。
到底一個母親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犧牲自己到什麼程度?我不知道,但是假如我媽媽在我們三個小孩都大一點之後,沒有出去工作,而是一直在家照顧哥哥的話,我相信她一定會得憂鬱症。倒不是因為她真的有事業心,而是白天固定的工作,讓她即使晚上回來仍要自己照顧哥哥,至少有機會喘息。
看著母親這樣一路走來,我雖然打從心裡心疼又敬佩,但是我知道,母親會走上這條路,也不是她自己選擇的。長大接觸女性主義法學理論及社會福利法,更讓我期待有一天這個社會可以更平等:父親、祖父母、親友、社區與國家能夠跟母親一起照顧孩子,而不是坐視媽媽們犧牲奉獻自己的人生,然後廉價地感嘆著「為母則強」,或者每年母親節送個卡片蛋糕意思意思一下。
我的母職實踐
因此我成為兩個女兒的母親時,我知道自己既沒有那個體質,也沒有意願當一百分媽媽。我希望自己能夠給孩子「所需要」的愛與照顧,但仍能保有自己對生活與工作的主體性;我希望跟孩子有親密的親子關係,但是協助孩子有能力自己照顧自己。
儘管存著這樣的照顧理念,孩子當然不可能一生下來就獨立。相反地,有小孩之後,生活的許多瑣事,不是一條線,而是永恆的鬥智鬥力。以吃飯為例,餵食可能只要十分鐘,而且桌面比較整潔,但你知道你必須等待她們自己做,培養她們自己照顧自己的能力,有一天才能從這些事情解脫,因此你得花四十分鐘。而且在好說歹說之後,掙扎著要不要再多努力一點逼小孩吃青菜?要不要繼續提醒坐姿或餐桌禮儀?飯後碗筷或桌面的清潔呢?何時該尊重?何時該堅持?如何尊重或堅持?……然後在這一切的角力與盤算之外,還要自己找空檔盡快扒完自己的飯。這還只是吃晚飯。類似的考驗,每天從起床盥洗、早上出門到接孩子下課,吃晚餐、寫功課到睡前講故事的儀式,應付完這些事之後,個人需求被壓縮到最基本的滿足,不太有心情與時間考慮自己想穿什麼、想吃什麼、想做什麼,因為自己的時間用在小孩身上之後,已經所剩無幾。
而且,無休無止的征戰,也存在於自己的內心,儘管知道自己不想也不必當一百分媽媽,但是當女兒意有所指地說,同學的媽媽中午放學,都會來校門口接她們的時候,必須重新掙扎與評估:我是不是一個壞媽媽?或者要不要當一個沒有生產力的學者?兩者拉鋸的罪惡感,逼我從一個有獨立自我有夢想的女性,不得不正視小孩吃喝拉撒睡這些最直接的需求,放下自我的耽溺與虛榮,不斷地在自己跟孩子的需求之間妥協,最後夢想變得很單純:希望孩子健康快樂地長大。

母職與教職的交互影響
在這些母職的征戰之中,我知道我是幸運的。大學教師的工作型態讓我對時間與工作品質有很高的自主性,丈夫、母親則是我堅強的盟友,還有幾個有同齡孩子的朋友們,週末一起帶孩子,讓我儘管時時必須面對這些內在外在,但從結果而言,兩個女兒一個九歲、一個十二歲都尚稱健康快樂,而且跟我有很親密的關係,儘管過程中起起伏伏,但我還是熱愛我的工作與母職。
但是有孩子,對我作為一個大學老師有幾個影響。影響之一是,因為和小孩打交道久了,學會用淺白的語言解釋這個世界,重新思考許多理所當然的事情。例如「為什麼人該有禮貌」、「那社區散步時跟陳爺爺打招後以後,需不需要跟後面沒那麼熟的叔叔打招呼」、「長頭髮的一定叫阿姨嗎」……,因而反省了許多原先理所當然的眼光,讓我面對學生奇怪的問題,更能包容。
影響之二是,因為配合小孩的節奏過日子,相對時間變得零碎了,因此習慣同時多工處理許多瑣事、習慣面對混亂、習慣在完成與不完美之間妥協,甚至因為常常同時要協調先生、媽媽與孩子的照顧行程,也一併習慣處理人際關係。但在工作上儘管胸懷大志,因為心思與時間不能完成交響曲,只夠做小品,結果常常連小品也難產。
影響之三是,因為常面對有限的時間、衝突與實際的人,我對於抽象但沒有人味的理論抱持著更多的懷疑 — 一定要知道實際的人是怎麼過日子,才會信服那個論述。
影響之四是,儘管時常在育兒不力與工作不力的罪惡感之間掙扎 — 而且至今還是在兩者之間跌跌撞撞 — 但一路走來,還是重新認識並肯定「照顧」在社會中的價值。
其實,粗略估計,我學術界的女性朋友有超過一半以上沒有結婚;有結婚的那一半,則有一半沒有小孩,至於有小孩的,也大多只有一個小孩。這讓有兩個小孩的我,面對朋友紛紛升等,以及自己落後的學術產出,常覺得很心虛、自己很不「專業」。
不過,隨著少子化變成國安危機,儘管政府對托育的協助還是如杯水車薪,但是至少在為了育兒而無法出席週末的學術或服務時,心理上稍微少一點罪惡感。這種沮喪的感受,直到有一回帶孩子參觀柏林國會,現場人員引導帶小孩的人,可以越過長長的人龍,優先上電梯參觀國會,才真正感受到帶小孩的光榮感。
於是,在我負責的「醫學人文導論」第一堂課,我開始略過耶魯法學博士及研究專長等耀眼但空洞的名詞,在全體醫學系大一新生面前,列出自己帶兩個小學的小孩、陪伴一個腦性麻痺的哥哥長大、照顧生病的公公與骨折的媽媽、幫小孩照顧獨角仙和孔雀魚,並守護一個花園等等的「照護履歷」,跟同學介紹我自己。我發現自己第一次可以理直氣和地跟未來即將照顧許多病人的醫學生們說,其實關懷照護(caring)的工作無所不在,所需要的能力也一點都不高深莫測,不必等到有醫師證書,現在就可以培養自己照顧關懷別人的能力,就從身邊的人做起。醫療工作,不就是健康照護(healthcare)嗎?假如一個人連身邊的親友都不關懷的話,怎麼可能真心去關懷照護陌生的病患,並且當作一生的志業呢?
也是從那時開始,我重新認識了「關懷照護」的意義:我的母職經驗雖然讓我在工作上不良於行,但是我除了享受到陪伴兩個孩子成長的快樂,也真實地體驗到關懷照護工作一直被自己跟這個社會低估的事實,以及它的重要性。雖然我們的社會或身分賦予我們照顧家人的義務,但當我們真心關心一個人的時候,其實不是為了義務或罪惡感,而是因為愛,也因為「我們」這樣一個共同的關係。
所以對我而言,母職因此是一種承擔:承擔孩子在獨立之前,成長茁壯所需要的養分。在實踐屬於自己的母職理念時,我也希望任何母親都不需要強悍,也不需要孤獨,而是能夠有許多人一起分擔照護孩子的甘苦,而每個母親也都還是能有自己其他的夢想與生活,一起成就一個充滿愛與關懷的社會。
但願有更多人跟我一起實現這樣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