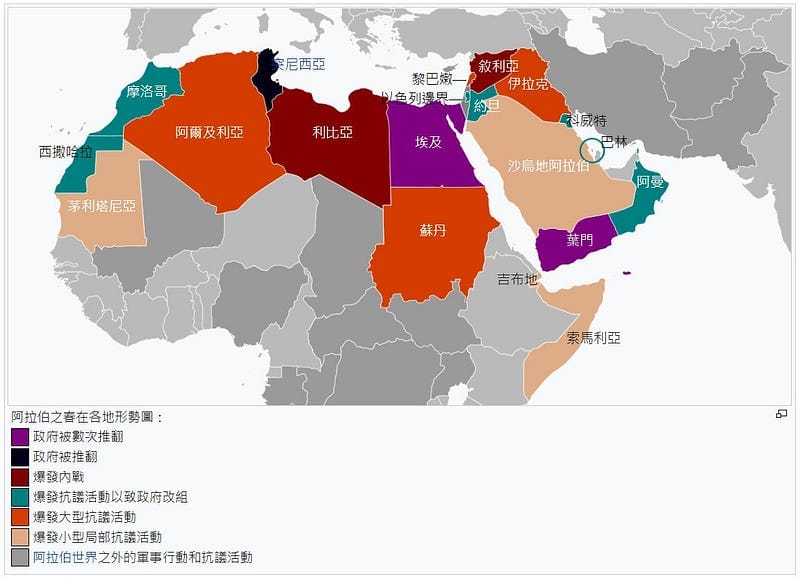特別企劃 / 新二代留聲機
劉俊良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碩一生
在許多新二代的生命經驗中,當人生開始向家庭之外發展,例如進入學校或其他環境,我們才驚覺自己有位「與眾不同」的母親,而我們也得接受現實──在這個社會裡,某些人好像並不怎麼喜歡自己「特別的」母親,甚至他們的不喜歡還會蔓延回到自己身上。因此新二代們做出了選擇,有些人致力向他人介紹自己的母親以及母親家鄉的文化,希望打破誤會、破除污名;也有些人選擇將自己的背景與母親盡可能的隱藏,冀望這些特別之處隱藏起來以後,污名便不會找上門。
我過往也曾經是選擇銷聲匿跡的一員。早在國小的年紀,便意識到中國籍新住民母親的污名,且深深的陷入與之抵抗、掙扎與拉扯的成長過程。直到多年後我漸漸與自己、母親以及那段回憶「和解」,並寫出這段往事,讓更多人知道一位臺&中新二代的生命故事,希望能鼓勵有相似經驗的人擁抱複雜、多元但真實的自己。
隱藏與現身的拉扯
約莫從國小一年級開始,我便能從與人的互動中感受到他者對中國的那股「令人說不上來」的奇怪反應,無論是班導師在課堂提高嗓門、高八度的問我:「你媽媽是中國來的?」或是同學聽聞此事之後詫異且帶著距離感的神情。當時恰逢「中國三聚氫胺毒奶粉」新聞籠罩全臺,雖然才小學一年級的我,不會知道臺灣社會因為這起事件對中國的反感更為嚴重,但仍憑著「小孩的直覺」,下定決心向他人隱藏「媽媽的存在」以及「她來自中國」。因此往後的幾年裡,凡是老師、同學討論到「初二回娘家」或任何關於母親的話題,我都竭盡所能地閃躲、裝傻,也用盡各種方式阻止媽媽參與班級家長會。不過這樣的想法,在我升上五年級之後發生了改變。
新的班導師非常鼓勵家長們參與班級的各種事務,舉凡運動會、園遊會和各種班際比賽,部分家長亦積極響應老師的號召。在這樣的班級氛圍當中,自己的家長參與班級事務是件在同儕之間很值得驕傲的事,因此我在經歷一陣心理掙扎之後,向媽媽提起了希望她能參與班級事務,而她也在我三番兩次的要求之下,加入了參與班級事務的家長的行列。接下來的日子裡,母親參與班級事務確實讓我受到老師的讚賞以及同儕的稱羨,不過那個令我困擾的問題也浮上檯面,同學們開始注意到媽媽的口音,時不時有人向我丟出「你媽媽是不是大陸人?」之類的問題。
雖說我在要求媽媽參與班級事務前也掙扎過她的「口音問題」,但是我沒有料想到媽媽那個以我聽來「不怎麼明顯」、「應該不會被發現」的口音,原來在同學耳中是那麼明顯、特別。我更沒有料想到,同學們試探性的好奇居然如此輕易地將我推入焦慮的深淵。然而我不知道該如何向媽媽表達我的焦慮,我曾不只一次聽聞媽媽與我分享她因為「中國人」的身分而受到的不平等對待,所以我不敢、不忍、也不願意告訴她「妳的身分讓我在同學間很困擾」,我只能不停暗示媽媽不要再參與班級事務。但是這並沒有用,她沒有意識到我的不安,仍熱情投身於「積極參與班級事務的俊良媽媽」。這成了我們親子關係的隱患,並在我升上國中之後徹底爆發。
關係的決裂──揮之不去的口音
隨著我進入國中階段,母親依舊是那位出現在班級活動的「熱情的俊良媽媽」,但是新的同學和班導都意味著環境以及規則的改變,此時媽媽參與班級事務再也不會讓我受到班導師的讚賞,或是在班級中享受羨慕的目光,剩下的只有同學們對於她的、令我不安的好奇:「你媽媽說話怎麼聽起來怪怪的?」
此時的我仍沒找到適合的方式向她表達我的焦慮與不安,所以我選擇在她出現時躲得遠遠的,就好像只要我與媽媽沒有在同個空間同時出現,她就不是我的母親,而她的口音與我無關。但同學們的好奇並沒有因為我的鴕鳥心態而消停,反而全班都注意到「俊良媽媽」每次都會用她特別的口音問同學:「有沒有看到我們家俊良?」
我原先不希望大家注意到媽媽的口音,現在她的口音卻變成全班皆知的事。這個滑稽的狀況直到某次學校園遊會結束,一位同學私下突然跑來問我:「你媽媽的口音聽起來像大陸人,她是嗎?」這個問題成為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或許對方只是出於好奇而試探性的詢問,但我在當下猶如驚弓之鳥,心裡不斷想著:「完蛋,事情要暴露了!」於是在搪塞那位同學的試探之後,我決定在當晚向媽媽攤牌,我要用盡一切方法阻止她「毀了」我的校園生活。
矛盾的集合體
晚餐時,我向媽媽「發難」。我把自己從小學一年級以來所累積的,因為她的身分而受到的委屈,以及她頻繁出現在學校對我造成的焦慮與不安,一股腦的使勁朝媽媽丟去。初入叛逆期的我已經習慣因為各種日常瑣碎的雜事與母親大聲嚷嚷、謾罵,原以為這次她也會以同樣高漲的情緒回應我的不滿,然而在我一陣「情緒輸出」之後,媽媽並沒有如我預期般的憤怒,我只從她的眼神中感受到對兒子的失望,以及一句冰冷的:「你就跟外面那些人一樣,那麼討厭我嗎?」
言畢,媽媽匆匆收拾自己的碗筷便離開了餐桌,我則伴隨著時不時從媽媽房間傳出的啜泣聲,以及自己逐漸冷靜的情緒,陷入了記憶的漩渦。我回想起媽媽如何遭到同事排擠,如何因為口音而被客戶刁難,以及種種因為「中國人」身分而受到的不公平對待。我原以為媽媽是主角、是受害者,那些欺負她的人是壞人、是加害者,而我只是這些悲慘故事的聽眾。然而經歷了剛才的事件,我意識到自己不只是旁觀者,有時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會被劃分成「中國人」並遭受討厭,甚至有時,我會因為害怕被劃分為中國人或聽聞媽媽的經歷之後,內化了社會對待她的錯誤觀點而成為壞人。
就在前一刻,我從媽媽的兒子、她的聽眾、她最柔軟的那塊,搖身一變成為了增加她痛苦的加害者。然而,即便我想通了自己、媽媽以及這個社會的互動關係,我明天仍要面對同學的好奇與試探,因此我咬牙告訴自己:「雖然很對不起,但我猜媽媽『學乖了』,她應該不會再去學校了。」我決定把才釐清的關係打亂,以此忘記自己不只是個當事人更是加害者,並假裝仍是置身事外的旁觀者。
從社會學的知識到母子關係的和解
往後的日子裡,我與母親有默契地未再提起那晚的事,我也鮮少和媽媽聊天、聽她傾訴種種不公平,我慢慢地與「旁觀者」的角色漸行漸遠,幾乎成了和新住民、新二代身分毫無關係的「局外人」,不過這一切在我進入大學階段再次改變。大學就讀社會學系的我,受所學知識影響開始閱讀新住民相關的研究,我在文本裡看到新住民如何受到國家制度的排擠、或受到新聞媒體的污名,或承受社會大眾的歧視,文本所刻劃的每一位獨身來到臺灣努力生活的女性,不斷與我記憶中母親的身影重合,加深了身在異鄉的遊子對母親的思念,更喚醒我對媽媽的愧疚,最終,思念與愧疚的堆疊,驅使我第一次主動撥通打給媽媽的電話。
不過,這通電話並不如我想像中的坦承與悲情,作為一名「經典的」受到性別氣質的束縛而被剝奪了情緒的男性,我似乎不擅長表達內心對於母親的想念和愧歉,我只是一個勁的跟媽媽分享自己在研究中讀到的新住民的「慘況」,最後才勉強擠出一句:「我現在才知道你一直以來有多辛苦,對不起。」便草草結束話題。
雖然關於「我們的身分」的第一次對話並不理想,但我與媽媽還是在這樣的契機下重啟了這個話題,在那之後,我們愈發頻繁的通話,我也在過程中練習把內心那些以前不知道如何啟齒,或因為過往行為而產生的愧疚傳達給媽媽,我想為小時候的懦弱道歉,為當時沒選擇站在「母親那一邊」甚至傷害了她的自己道歉。然而媽媽卻告訴我:「小時後的你所做的那些行為並不是懦弱的表現,你只是選擇先保護自己。」除此之外,媽媽更說她從未想過要怪罪我,她知道這些是人生的必經之路,她選擇耐心的等待,並相信有一天我會更加強大與自信,找到和自己、和母親「和解」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