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突然有一天,我成為了女性主義者
張桓溢 / 本刊編輯
廣場封鎖線的外側,她站著,像一枚距離剛好的衛星,看系上的學長姐或肅穆靜坐,或昂揚地喊著「解散國民大會」的訴求。
那是1990年,野百合運動在尚未改名的自由廣場上爆開。18歲的姜貞吟剛進到東吳社會系,便跟著學長姐走至了抗爭的現場。前一年中國發生的天安門事件,使她第一次看見了「國家」與「社會」對個體的影響,但當那個於課堂、讀書會中被反覆思索與詰問的「結構」,突然近得彷彿伸手就能觸摸、甚至被撼動,她仍然有些遲疑,不確定自己是否已經準備好投入至一場運動,或者說,面對抗爭可能的後果。
「因為不知道自己進去後會怎麼樣。那時候才解嚴沒有很久,每個人都是很嚴肅地在對待這件事情。」在解嚴但尚未撤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臺灣,表達自己的意見與立場,並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許多轉變仍然有待時間催化,對姜貞吟自己來說亦是如此。
文學少女的彼時陣
畢竟以前的她不知道「政治」,也沒聽過黨有內與外的區別。國、高中時代她讀最多的,其實是文學。既看朱天心、七等生,也讀楊青矗、王禎和的小說,通俗一點的倪匡和瓊瑤要看,三毛的書更是一本都沒落下。曾經她試過寫作,(自謙)因缺乏天分而放下,長大後卻仍會循著作品中提及的地景,尋訪那些縈繞青春之夢的遠方。
當然,如今的姜貞吟已然可以透過各種精準的語彙,詳細地指認階級、族群乃至性別,如何交織於她的成長經驗,形塑她認識世界的眼光──譬如她的父親是跟著國民黨渡海來臺的軍人,雖然沒有入住眷村,但對中國故土仍然具有強烈的情感連結,這部分驅使她閱讀抗戰、離散相關的作品,索驥父輩的身世;她的母親則是在臺南玉井長大的閩南人,從小浸染於道地閩南文化的姜貞吟,遂從鄉土文學中尋見自己生活的景況。
只是上述這些,畢竟都是「啟蒙」後才得以辨識出的軌跡。在學會詮釋的語言以前,一切仍處於混沌而未明的狀態:她只是經驗著。姜貞吟記得阿嬤過世的時候,母親帶著她跟妹妹,從巷子口一路跪著爬進靈堂,「可是其他表哥們都是走著進來。怎麼會是我媽、我跟我妹要跪著進去?這個印象很深刻,我就問為什麼。那時我得到的答案很單純,就是女兒嫁出去後,就不再是本家的人了。」
講起來有點心酸,有時習俗僅僅因為「大家都是這麼做的」被實踐。年幼的她得不到更多解釋,卻一直在心中記得這個、「因性別身分不同而被差別對待」的時刻。
類似這樣的困惑,形成了她生命經驗中無處不在的氣泡。直到大學時接觸了性別研究,這些細微的氣泡逐一浮起,她才漸漸看見裡頭包裹著差異的空氣,究竟來自何處。
生活作為研究的起點
讓這些氣泡浮出意識水面的關鍵,或是她大學時擔任劉惠琴老師的計畫助理,在老師的引領下,開始接觸性別理論與相關研究。以新的語彙回顧自己的成長軌跡,姜貞吟發現,原來「性別」,一直以一種可見卻不可盡見的形式,影響著她的認識與行動。譬如高中時自己「理所當然」地選擇了人文類組,或者看著母親及其他女性長輩在職場與家庭的模樣,以為那就是自己將踏入的未來;種種這些,因為身為女性,所以被不假思索接受的座架,恰恰就是性別理論所欲探問的對象。
於是,最私密與最日常的生命經驗,遂成為她研究性別的起點。也或許,所有性別研究都是從自我的生活出發的。因為「那個性別的深刻,必須隨著你生命不同事件的經歷,才發現它是如此的深刻。譬如說我要爬著進去巷子,我才知道我是女的所以我要爬進去……如果我沒有這個經驗,我就不會知道性別對我的限制是什麼。」姜貞吟的碩士論文探討性別與勞動的關係,某種程度便是為了理解母親經歷的女工世代,與階級、性別等因素加諸在母親身上的限制。
但跳出來阻止她去國外攻讀學位的,也是母親,「她說,她不知道女生唸那麼晚還不結婚到底要做什麼?還可不可以有一個幸福的未來?」說起這段往事,姜貞吟的語氣裡,更多是一種通透的包容。儘管後來憑藉父親的支持,她順利到法國留學、完成學業;但如果連女性自身都以為幸福僅能由婚姻來保證,那麼這個「幸福」的價值顯然需要被挑戰,並且重估。
只是這項工程不僅僅需要更細緻的研究論述,更需要介入。姜貞吟說,自從她下定決心踏入性別研究之後,身邊一些女性朋友開始會主動向她分享自身的生命經驗。聽了這些或關乎迷茫、焦慮、無力乃至創傷的敘事,她意識到,看似冷硬的理論或倡議,其實亦可以是賦能受壓迫者的資源──只要它能夠轉化為日常的語彙,甚至是援救他人的繩索。
尊重,同時行動
性別研究因此是從生命出發,再回流至生命。返國以後,姜貞吟除了加入女學會與婦女新知,投身女性主義實踐的前線,在任教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後,更扣連客家族群議題與性別,於客委會擔任性平專案小組委員期間,積極推動「姑婆回家」,向客家文化的喪葬禮俗中、定義並框限二元性別的的傳統框架,敲響了改變的第一聲鼓。
由於所謂禮俗總是關乎特定族群/共同體的維繫,姜貞吟很清楚,相應的改變「必須深入跟各成員討論,而不是站在外部去批評他們。」每個族群都有其在歷史中形成的獨特文化,不能以一種去脈絡化的史觀或立場,否定這些風俗習慣之於個體的意義;而應該試著理解,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中,人與人究竟如何關係。
但這是否意味著,所有差異的文化習慣、儀式乃至觀念,終只能以一種相對主義式的立場「尊重包容」之?姜貞吟肯定地答覆我的疑問,她說,並不是這樣的。作為一名女性主義的實踐者,她仍然有其堅持的價值,仍然有其想望的「更好的世界」。畢竟,若非心中有其肯定的價值,則一切對話根本不可能發生。
只是堅持自身的理念與價值,並不等同於輕易否定或蔑視其他群體的存在與主張。一切改變皆須要更耐心的對話與溝通,如此才不致使那個理應「更好的世界」,成為眾人不想要的世界。
「所以,至少我會非常尊重時間的進程,而且是內部的進程與內部的選擇。」這是姜貞吟在「應然」與「實然」之間摸索出的心得。平等需要時間,正義需要耐心。儘管這有時,難免會挫折或沮喪行動者,她倒是看得很豁達。
「臺灣這20年來進步得非常得快。其實我們已經高度壓縮時間的進程了。」她如是正面看待臺灣在性別平權路上的努力。
盡己所能
興許是這樣的耐心,2022年起正式接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一職的姜貞吟,談起組織進行各類議題倡議時,經常要面對的理想與成效間的落差,也沒有太多憤懣和焦慮。她深知,建立或修訂關於「平等」的法規,哪怕只是從「兩性」到「性別」這樣看似輕簡的改動,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與倡議下,才取得一小步一小步的進展。
說來平靜,實際推動的過程卻近乎前仆後繼。以婦女新知爭取有薪「家庭照顧假」的過程為例,自2011年以來,婦女新知便聯合各團體,要求修訂《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0條,訴求的是軍公教及勞工均可請14天有薪假¹,或勞工比照公務員待遇,能請7天有薪假。如此提出訴求10年有餘,儘管成果有限,婦女新知的發聲卻未曾歇止。
[1]依目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0條規定,家庭照顧假係併入事假計算,且全年以7日為限;又依勞工請假規則規定,勞工事假全年以14日為限,且事假期間不給付工資。換句話說,家庭照顧假不僅未能滿足原先支持家長照護家庭的立法目的,更使勞工背負無薪的不利益。
「無論如何,我們要告訴政府的是,7天真的不夠用,請你認真以待。勞工是需要足夠的家庭照顧假,來照顧有需要的家庭成員的。」
重點是「認真以待」,進行倡議的同時,姜貞吟說,他們其實也正努力向社會說明,這件事情為什麼重要。因為,正是透過這些法令與規範,生活才對某些人形成了難以迴避的負擔與壓力。
這樣想來,所謂女性主義者,其實便是對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皆「認真以待」的人。這是知識的實踐,也是關乎實踐的知識。婦女新知參與或推行的每個議題,都是歷經團體內部成員反覆的討論,才形成共識,這為的便是將女性主義共生與平等的精神,具體落實在組織內的運作之中。
而這,或許才是最難的:不將對話、協商的過程僅僅視作手段,而是時刻警惕自己,過程即目的。如此,無論是研究、言說、工作抑或待人處事,無一不關於性別理論的操演。這是姜貞吟從性別圈的前輩們身上習得的,而今她以自身的日常踐履之。
因為價值就在生活裡,「當它(女性主義)是我的信念的時候,我在很多行為,我跟人的互動,它就會是那個樣子;我不會因為對方是什麼階級,我就對他有不同的態度。」這大概是為什麼,整場訪談,竟也能變得像是意見的往返,允許訪問者如我,拋出各式其實是關於自己的困惑,而仍然能被溫柔地回擲。
其中一個特別艱難的問題,是這樣的:我問姜貞吟,我們如何可能重新想像一種「自由」,作為主體行動或決斷的基礎?她笑著回我,這個問題,她在10多年前也會不斷地想,但現在已經不太想了。如同史碧瓦克(Spivak,2006/2021)說:「我不像從前那樣動輒想改變世界了。」姜貞吟現在將更多精力放在如何修正法律,保障個體不會因為性別差異,影響自身應有的公民權益。
畢竟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姜貞吟停頓了一下,又說,不過也很可能因為忙著做這些細瑣的事,忽略了從更高的層次來回應社會的必要性──言下之意是,思考這類的問題也很重要。但無論如何,她就是在她身處的位置上,盡己所能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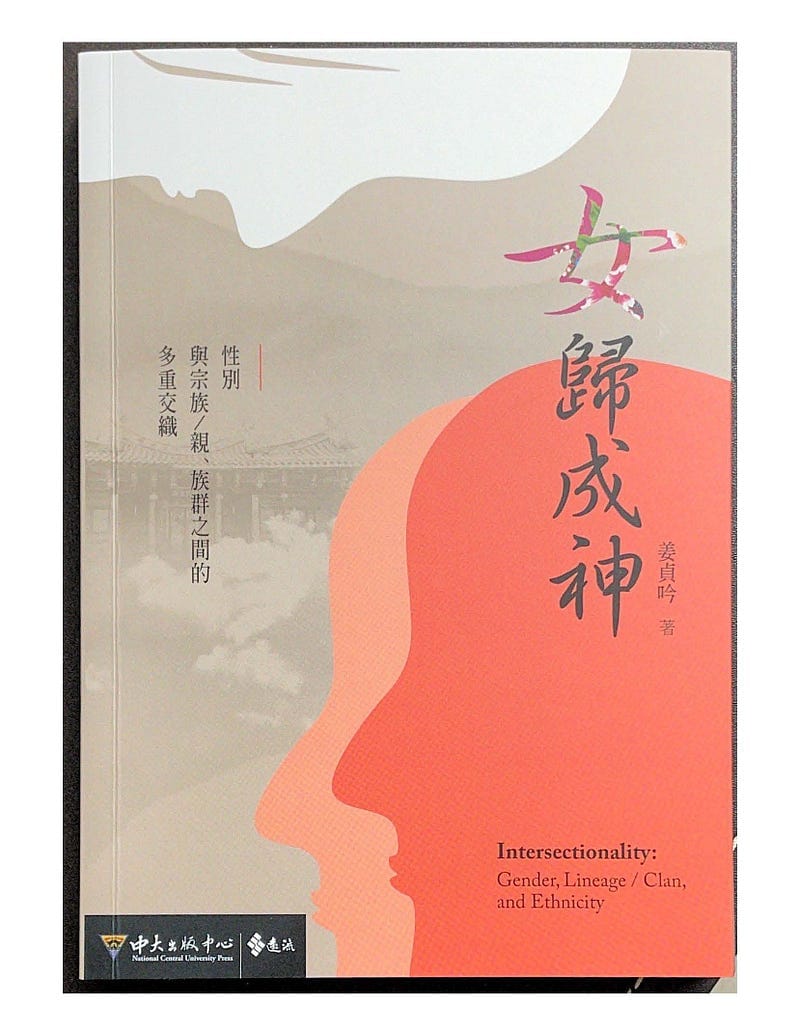
參考文獻
- Spivak, G. C.(2021)。在其他世界:史碧瓦克文化政治論文選(李根芳譯)。聯經。(原著出版於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