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現場/一「同」現「聲」
採訪 / 蕭宇、李耘衣
撰稿 / 蕭宇 (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 )

訪問那天,我們在約好的下午走進打烊的餐廳,陳釩和員工、友人正悠閒坐著聊天。陳釩和穆德在2007年結婚,婚後陳釩向朋友借精、自己滴精受孕,2010年生下老大蛋捲。蛋捲出生後,陳釩辭去原本幼兒園老師的工作,當起全職的家庭主婦。蛋捲3、4個月大時,她們舉家從臺北搬回臺南並創業,之後陸續生下老二奶昔和龍鳳胎藍莓與貝果。這間餐廳是她和穆德共同打造出來的堡壘,就好似她說要在體制內衝撞出同志家庭的空間。
披荊斬棘的生子之路
陳釩受訪的經驗並不少,上網搜尋,可以看到各大主流媒體都曾出現她的名字。訪前,我一篇一篇讀過,透過文字影音,能感覺到陳釩對同志及同志家長的身分有著明確的想法和縝密的規劃。個性優柔寡斷的我,忍不住一坐下就問她怎麼總是如此堅定,陳釩說:「我很明確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所以我做很多事情、很多決策,都是非常有目的性的。希望有策略地去追求,才不會浪費時間。」
這種遇到問題便開始分析、規劃並執行的性格,在懷孕生子這件事上發揮得淋漓盡致。2007年,陳釩和穆德辦完「婚禮」後,媽媽就問她要不要收養孩子。陳釩迅速地花了兩週調查,發現收養這條路並不可行,因為她和穆德當時沒有法律上的婚姻關係;接著換婆婆說想當阿嬤,問陳釩什麼時候要「生」小孩?這一問開啟了她對於生育的想像:「那時候我才發現,我自己生?要跟誰生?我婆婆說,我管妳跟誰生啊,重點是生一個出來就對了。我才意識到,原來長輩是可以忽略血緣這件事情的。」我問她這樣算不算是迫於上一代的壓力而生育?陳釩毫不猶豫地否認:「我們沒有壓力,完全是樂意在做這件事!婆婆只是讓我去想到這件事;我自己早晚也有可能會想要生小孩,只是沒那麼快。拜託,我們才剛結婚兩個禮拜,哪有那麼急啊!」
接著陳釩開始蒐集資料,以懷孕為目標。她上網查「女同志」、「生小孩」等關鍵字,國內、外的資料都不放過;學著算排卵期、記錄基礎體溫,甚至學會自己判讀賀爾蒙數值。連如何找到符合需求的醫療院所、如何在與醫護人員的對話中適時利用異性戀傳宗接代的文化引導風向,陳釩都在腦中有一套清楚的戰略。她懷胎三次,每次都得運用不同的策略。聽她繪聲繪影地描述這段經歷,口中連珠炮蹦出各種專有名詞,旁聽的我們像是在看鬥智電影,佩服不已。
敬佩之餘,我心中也感嘆策略背後的不得已。礙於同志家庭不是國家鼓勵生育的對象,這些資訊都無法大喇喇地走進診間索取,更因為臺灣可參考的先例不多,陳釩必須大量閱讀法條、醫學等各領域的資料,自己判斷、摸索。生育對她和穆德而言,必定不是條好走的路。如此披荊斬棘的生子之路,陳釩講起來卻是笑聲不斷、總能找到有趣的關注點,譬如當時她拿男同志朋友的精液去檢驗所「洗精」,以篩去活動力較差的精子並加入培養液,一來是對精子活動力有幫助,二來讓液體增量、自體滴精會更好操作。陳釩笑說:「培養液顏色每次不一樣,上次是藍色,這次你拿到變成粉紅色的。」
創造「一線生機」的註生娘娘?
雖然她現在講得一派輕鬆,但試想十多年前要找到這些資訊何等不易。儘管她在試著懷第一胎時國內已經出現女同志網路社群,但沒什麼人在討論生小孩的事情。陳釩說:「我在圈內問人,大家都覺得妳有病嗎?自己當同性戀也就算了,為什麼還要……連同志都對自己有汙名,所以我那時沒有辦法跟別人討論生小孩這件事該怎麼做。」但當然不是只有她們有育兒的夢想。後來,她們透過當時的「pchome新聞台」結識其他拉子媽媽,一對拉一對,慢慢發展到現在已是個一百多個家庭的社群。這些經驗的集結和分享,也開啟了很多女同志生小孩的契機,讓她們發現自己還有條「生」路可走,創造一線生機。陳釩也苦人所苦,讓自己的資訊非常公開,成為想生育女同志們容易搜尋到的詢問管道。有些人會直接私訊她:「我在報導上看到妳的名字,我想生小孩。」陳釩也是二話不說,從教授怎麼計算排卵期、月經第三天去檢驗賀爾蒙數據,連檢驗項目、細節開支一併傳授;有些人把報告拿給她看,請她協助判斷接下來是該去診所還是DIY(指人工滴精受孕)。陳釩說:「不認識的人,我也會約對方碰面。有些想報復性懷孕、或用孩子綁住情感關係,我還要幫忙踩煞車。」我們開玩笑說:「如此一來你豈不是引領眾女同志生子的註生娘娘?」

究竟是什麼動力讓陳釩願意大方分享她的經驗,陳釩說:「我當初走了很多冤枉路;不知道要驗賀爾蒙、不知道要看輸卵管、要看子宮內膜,我有很多不知道。在我從小的家庭經驗和生活並沒有遭遇太多挫折,最大的就是嘗試懷孕這件事;我花了太多精神在試錯,但這是可以避免的。所以能幫別人少走一些冤枉路我就幫,這對我來說並不會太困難。」這條坎坷的求子之路,陳釩將挫折轉化成為可以被散播的經驗,而她自己也從養育中獲得不少樂趣,儘管在第二胎受到難產之苦,仍堅持繼續懷孕,生下藍莓和貝果。
同志教養,既相同也不同
陳釩與穆德一家六口,她們在孩子接續誕生後,會因為同志身分而在教養上有所不同嗎?陳釩認為,同志家長帶孩子很關鍵的一點是「出櫃」,出櫃這件事是與孩子建立信任關係的重要機會,「我們會跟家長說盡量能出櫃就出櫃,至少對孩子要坦白。我們家老大蛋捲就很清楚,她是我們做IUI(Intrauterineinsemination,人工授精)生下的孩子。蛋捲會問捐精者是什麼樣的人,我會跟她講一些客觀條件,例如身高體重等,問她會想知道是誰嗎?蛋捲有點好奇,但她覺得不知道也無所謂。我跟她說我們大人之間的協議是等她滿18歲時會告訴她,但在那之前不會透露。我講得很明白,所以她也不會覺得問我不行、就去問別人。」
陳釩很早就開始跟孩子解釋她們同志家庭的身分,譬如讀繪本時常見對家庭的描繪,陳釩會清楚地跟孩子解釋,自己和穆德是有婚姻關係的,而且是先結婚才生下孩子們,算是一個「大眾」的流程。透過一次又一次地解釋自己家和別人家的相同或不同,不但讓孩子更清楚自己的定位,也讓孩子知道,我們與別人也有很多共同點;畢竟,每個家庭都是獨特的。
此外,出櫃也是為孩子在世界上撐出一個空間的必要行動。因此當老大蛋捲升國小時,陳釩和穆德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老師溝通,表明自己同志家長的身分。但出乎意料的是,她們並沒有遇到太多的異樣眼光。陳釩說:「我感受到來自學校的不友善程度是很低的,蛋捲也沒有因為來自同志家庭而遭受到任何批評,所以她對於自我的評價很高。我跟蛋捲說,雖然我們來自少數的同志家庭,但我們提供的環境算優渥;雖不是有求必應,但她想要什麼都可以提出來討論,是不是合理、是想要還是需要。無論是何種家庭型態,我覺得這是對孩子必要的教養方式。因此,蛋捲理解我們是用心在栽培她,她對我們這個家庭的認同度很高,在面對別人的質疑時,她會跳出來維護自己的家庭價值。孩子回應外界的的方式,與原生家庭很有關係。有些人會覺得同志家庭是社會上的弱勢,但我不這麼認為。我們在社會上怎麼是弱勢?疫情之前我們每年都可以出國,有能力讓小孩去學才藝,吃穿用度都能供應不錯的品質。況且我們家庭功能健全,雙親都很關心孩子。我跟蛋捲說,看妳用什麼標準分類,如果以雙親的性傾向來說我們是少數,但若你以小家庭、隔代教養、機構教養或大家庭這種分類,那我們小家庭反而屬於多數了。我覺得可以教孩子的太多了。要有多元的想法,但首先你家長要有足夠的sense啊。」
雖然出櫃是同志家庭的重要議題,但其實陳釩對教養的許多原則,並不只適用同志家庭,也適用於多數的家庭。同志家庭看似特殊,然而一旦聊起教養大家教孩子所面臨的困擾其實大同小異。這不就是社會原本的樣子嗎?世上哪個家庭是真的一樣的?社會上存有的不同評價,其背後的標準完全是人制定的。同志家庭當然不一樣,只是那個不一樣往往不是反同勢力所說的必須一男一女才能為孩子樹立模範的標準。
不卑不亢,在體制內撐出同志家庭的空間
當蛋捲要升國小時,陳釩並不像很多同志家長一樣考慮體制外的學習環境,而是讓蛋捲就讀離家不遠的公立小學。陳釩說:「公立國小就是大家的選擇,那為什麼別人家可以,我家不行?再者,因為公立國小是國家的,是大部分人遵守的遊戲規則,我們要在這個體制內開拓同志家庭的路,當我們在體制內我們才有可能產生碰撞,有碰撞才可能有空間。你沒有掙扎過怎麼會知道要在哪裡努力。」
雖然陳釩自認受到的反同壓力不多,但或許是因為她早已對自己的認同經過了縝密的思考和辯證,因此也隨時準備好與不同的聲音對話。譬如在2018年反同公投前,臺南路上隨時可以見到反同勢力的粉紅色布條,以愛家之名包裹歧視之實。我們問陳釩,蛋捲看了不難過嗎?身為家長,怎麼和孩子解釋這種惡意?
陳釩說:「那陣子蛋捲看到也是超不爽,她書包都會帶剪刀欸,隨時想要出去剪那個粉紅色布條。」但陳釩首先同理孩子,了解她的憤怒,再繼續對話:「我告訴蛋捲,其實可以不要這麼生氣,要理解對方背後的動機和脈絡。孩子理解之後還是有情緒要發洩啊,那可以看其他支持同志的人的做法,我也跟她說我朋友拿反同的傳單回家折成小紙盒再利用。這種反其道而行的方式,讓蛋捲聽了覺得很有趣,在她10歲的想法中,這就算是報仇了。」
待蛋捲心情平復後,陳釩嘗試再告訴孩子,每個人有自己的信仰和宗教背景,他們有他們信守的教條,而教條是經過後人轉譯過的,不見得完全真實或被曲解,但有些人相信了,認為同性戀是罪惡。我們可以理解他們,但我們也能不同意他們的看法。
面對孩子感覺被否定的挫折和憤怒,陳釩先接納、同理孩子,解釋之後再給予抒發的管道;這種處理的智慧,陳釩笑說和過去的教育專業及心理學經驗有關。而我們在這樣的親子對話中感受到的,則是對同志及同志家長這個身分的不卑不亢,讓多元的價值觀在下一代心中、在社會中一點一滴但穩固地扎根。
向下扎根,開枝散葉的多元價值
接近訪談的尾聲,我們問陳釩是否給學校和老師一些建議,讓我們社會的學習環境可以更友善。陳釩直接舉出學校發給新生的學生資料表格,她說:「表格是第一線的好不好,拿出點誠意來,《748施行法》都過兩年了都還沒改,表格上都還是『父母欄』,讓人家覺得很不友善啊。」蛋捲入學時,陳釩和穆德為了表格上的「父母」欄該怎麼填寫,苦惱了一陣子。
我們也談到現行學校的教材中時常以異性戀為預設,或是其他性別刻板印象。蛋捲對這些預設和刻板非常敏感,常對學校的課本「跳腳」,也會展開自己的反擊行動,「蛋捲會拿立可帶自己去改成她覺得比較公正的寫法,像她非常討厭『父母』兩個字,會抗議:『為什麼一定是父母?為什麼不能是父父或母母?用家長就好啦!』我會從脈絡跟她講,解釋作者的生平背景,蛋捲會覺得我很囉唆;雖然我傾向讓她去體會或了解一些事情,但蛋捲覺得現狀不ok就是不ok,她focus在現下這是不適當的。」
我們笑著說應該聘請蛋捲當教材審查會的學生代表。只是我心底十分感動,對10幾歲的孩子而言,要能自主產生這樣的行動力,不但要有足夠的自信、不自我質疑,還要有反抗的量能。這代表支撐在蛋捲背後的力量是堅定而且強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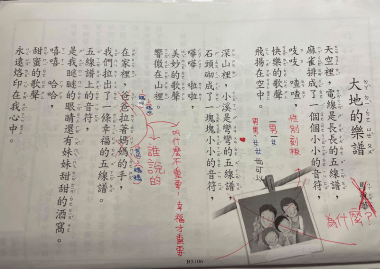
目前,陳釩擔任蛋捲就讀學校的閱讀志工。此外陳釩還提供了一個教學活動,建議高中老師可以徵詢班上同二代(同志家庭的小孩)的意願,看他們是否願意和同學分享來自同志家庭的經驗和感覺。陳釩認為大部分的不理解都是源自未知,她希望自己成為一個被看見的同志家長,因為:「人都傾向恐懼未知的事物。」她期許自己、穆德、她們的孩子,都要能夠站出來,也希望更多人能夠被看見,引發對話,促成理解與改變,這是她一直以來的理念。
見怪不怪,我們沒什麼不一樣
從陳釩自己當年為了生子所進行的隱身與各種摸索,談到孩子能夠自發地反抗不合理的體制,這一路走來,一再體會「看見差異,擁抱多元」這句口號講起來容易、做起來有多難。每個家庭都是不同的,但各種形式的差異卻獲得不一樣的對待:有些母親懷孕的過程很順利、而有些則否,這是很自然的情況;但同樣需要借助醫療的力量懷孕,法律卻將某些家庭隔絕在外;有些家庭是隔代教養、有些家庭家長性別相同,各自有不同的境遇和需求,這是多元發展的社會中再普遍不過的現象,而我們的社會、我們的體制充分承認這些差異了嗎?如今,法律上仍舊對同志家庭的生育進行排除,顯然還有許多需要努力的空間。
2019年5月17日,在《748施行法》正式通過,5月24日同婚專法施行當日,陳釩與穆德帶上蛋捲、奶昔、藍莓、貝果,一早8點半就到戶政事務所登記。兩人結束了「室友」關係,成為法律上的配偶。一家六口終於得以「團圓」,把全家的戶籍遷在一起。她們接著後續的繼親收養流程,讓穆德成為孩子們的合法家長。
最後問陳釩,蛋捲和同學的相處愉快嗎?她說蛋捲曾經跟她一位很要好的同學透露自己爸媽都是女生。她同學只是淡淡地「喔」一聲,沒有過多的反應。我們拍手叫絕,「這個見怪不怪,自然而然,才是正常啊!」
從陳釩與孩子們的互動中也讓我們看見,在同志家長與眾人的努力之下,我們的社會確實有所不同了。
- 蘋果新聞網女同夫妻搶登記:我們沒有不一樣:http://user129272.piee.pw/3krjnf
- 公共電視誰來晚餐第1季第19集女同志家庭:http://user129272.piee.pw/3k33d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