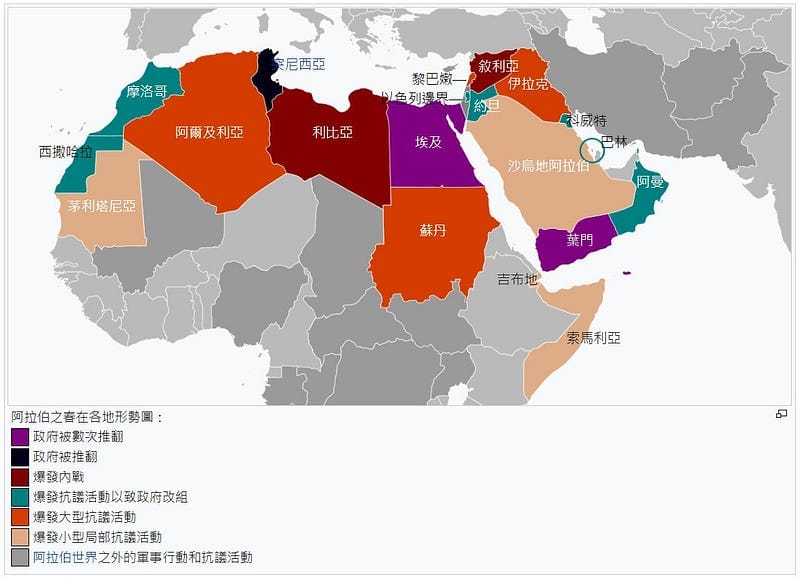專題企劃 / 新住民在臺灣
許育甄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大四生
曾獲第11屆新北市文學獎新住民文學創作組首獎,現就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四年級。
我是所謂的新二代。
每當我與同學或老師說起我是越南混血,大家的第一句話都是:「所以你媽媽是越南人!」
沒錯,我的母親是越南人,大家都是用肯定而非疑問的口氣,他們很容易就會猜到,從來沒人猜錯,不會有人認為我的父親才是越南人。
在我們的村子裡,上演很多相似的情況,他們全都娶了外籍新娘。阿公、阿嬤或是那些長輩們稱她們為「越南仔」、「大陸仔」。
這些娶了外籍新娘的男人們分成兩種,一種是年近30還沒結婚或是沒有對象的,另一種是60歲想找第二春的。
我的父親是第一種,右邊鄰居也是,而左邊鄰居是第二種。
運氣好的、夫妻間相處還行的,能安安靜靜過生活的,在這個村子裡稱得上是「幸福的」婚姻。但我沒這個運氣,我父母的婚姻是另一種,母親跑了的那種。
我的媽媽不是「跑了」
「你媽媽跑掉了,不會回來了,不要你們了。」
年幼的我聽著鄰居的閒言閒語以及阿嬤對於母親罵罵咧咧的指責,我不知道該呈現母親消失了的難過,還是要和阿嬤同一陣線義憤填膺,似懂非懂的我只好先隱藏著自己的情緒。8歲的我有一百個為什麼,但我問不出口;我有想說的話,但我不知道該如何在七嘴八舌的言談中,找到立足之地。
母親其實沒有跑了,「跑了」帶有不辭而別的意思,但她有告訴我她要回越南,不回來了,這應該不算是「跑了」,而是「告別」。母親離開時跟她來時一樣,總是那麼匆促。
當年母親是父親跟阿嬤慎重地搭飛機到越南「挑選」過來臺灣的,母親也就是所謂的「越南仔」。登機時,父親手中提著母親的大行李箱,飄洋過海來到東北方的小島,裡面承載的是新住民來臺的黃金夢。
母親來臺後的頭一兩年,與父親的關係極好,就像熱戀中的情侶一般,很快的兩三年內生了我和弟弟,此時在阿嬤的眼中,母親的任務已經達成。於是她被安排在村子裡的工廠中做一些簡單的手工活,無趣的日子久了,母親決定回去越南,不過她並不像阿嬤及鄰居口中那般的無情,雖然她一走了之,卻也留下了連絡電話。
她離開的那天是早晨的飛機,我起床時,她已經離開。
嬸嬸說,母親其實不如其他大人口中說的那麼狠心和糟糕,她嫁來臺灣無依無靠,我的父親又是個無聲的角色,她所有的生活都在阿嬤的掌控之下,她是有很多苦衷的。
「妳媽媽是比較喜歡到處玩樂,她是把你們留在了臺灣,但就算她真的要把你們帶在身邊,帶得走嗎?」
「你知道嗎?同樣身為嫁進來的媳婦,你媽媽跟我訴過苦,阿嬤只把她當成生孩子的工具。」
阿嬤曾說過:「沒有母雞不會下蛋的。」這是母親離開後的幾年,嬸嬸告訴我的。
無聲的兒子與丈夫
我的父親也稱不上是位稱職的丈夫,我和弟弟出生後他經常晚歸,甚至不回家,我曾經在睡夢中被吵醒,看見母親跪在放置家用電話的桌子旁,跟父親的朋友通話說:「我拜託你們請他回家好不好?」
在這樣失重的婚姻中,阿嬤對於父親的包容並沒有同樣呈現在母親身上,鄰居的指指點點也永遠只落在隻身從越南嫁過來的母親身上。
我想母親或許真的是「逃回」越南的。
我曾經撥過母親留下的那支電話號碼,那時我必須小心翼翼的溜到2樓,小小聲地與母親通話,告訴她我又拿了什麼獎狀、考試得了第幾名。當我結束通話下樓後,阿嬤會陰沉著臉問我:「妳剛剛是不是打給那個女人。」
漸漸的,那支號碼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我就這樣與她斷了聯繫,雖然家中的號碼一直沒變,但我也不曾接到那通越洋電話。
母親離開後,村子裡的日常還是照樣上演,誰家的老婆跑了似乎已經不足以成為街坊鄰居間茶餘飯後的話題了。
不公平的評價
幾年後,隔壁鄰居風風火火的娶了個中國籍的新娘,也就是所謂的「大陸仔」,他們辦了幾桌的好菜,邀請左鄰右舍一同來共襄盛舉這血統與文化資本嫁接的時刻。隔壁的阿伯是個老農民,60歲了僅靠著幾張照片就決定了牽手度過餘生的第二春,剛開始大家都對這位個頭嬌小、皮膚白皙的中國太太「印象不錯」。
然而這樣速食的婚姻,很快地讓阿姨發現了掏金夢碎。阿伯是個菸酒成癮的人,阿姨骨子裡有火辣強悍的個性,免不了的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鬧,雖然時常被不絕於耳的咒罵聲困擾不已,不過畢竟是別人的家務事,我並未多加留心。其他鄰居就不一樣了,他們比我「熱心」許多,紛紛到隔壁阿伯家,指著阿姨的鼻子,告訴她做人的太太氣焰不能那麼囂張,不能得寸進尺。
歷經那次嚴重的爭執以後,本來隻身到臺灣的阿姨在村子裡顯得更孤立無援了,她一人兼三份工,幫人打掃、做菜等等,偶爾隔壁還是會傳來阿伯的咒罵聲,但再也沒人去關心。後來,他們迎來了一個小男嬰,大家反而關心起來了,紛紛到隔壁阿伯家恭喜他,說阿伯是「老來得子」,阿姨在上次爭執後,也不與鄰居打交道了,鄰居對著抱著孩子的阿姨噓寒問暖,阿姨只是淡淡回應。
阿嬤跟我抱怨阿姨態度很差,看見鄰居也不知道要打招呼,每天擺著一副臉孔,好像大家欠了她多少錢似的。
嬸嬸說村子裡對阿姨的評價是不公平的,那些家務事不是外人可以理解的,在新的環境,縱使文化語言的差異並不是太大,她畢竟離鄉背井嫁到了臺灣,肯定有她的辛苦之處。嬸嬸還說,「我和叔叔從不對她惡言相向,所以她對我們的態度也是客客氣氣的。」
也因如此,阿姨時常尋求我跟叔叔的幫忙,來到異鄉,不懂臺灣的電信、不知道要到哪裡修電視、不會操作智慧型手機、不了解新冠疫苗該如何登記施打,在鄰居的不友善中她無法向周遭的人尋求協助,只能賭賭運氣在剛好遇到我們時,請我們幫忙。這樣的善意是雙向的,有一次我們臨時需要一串衛生紙,想要跟阿姨買一串,阿姨擺擺手說:「沒關係,直接給你們吧!」
此時那些大人口中輕蔑的「大陸仔」聽起來才格外諷刺。
沒有對錯、沒有單純的標籤
母親與阿姨最大的區別除了一個是「越南仔」、一個是「大陸仔」以外,另一個就是母親逃走了,但阿姨並沒有離開,她選擇了在臺灣這個小村落裡吃苦耐勞定下來。母親與阿姨的抉擇並沒有誰對誰錯,光是要背井離鄉遠嫁到陌生的國度,就須要有極大的勇氣,這是母親與阿姨同樣背水一戰的堅定。
我同情母親的遭遇,心疼她受到的那些不公平的待遇,同時我也敬佩阿姨的韌性,能夠堅強地支撐起她的丈夫和孩子。她們的跨國婚姻裡,夾雜著的是幸福、是謊言、是經過包裝的蜜糖、是拆穿後的失衡與不公,被貼上標籤的她們,在異國他鄉也曾是揣懷著夢想的人。
我的親生母親來自越南,是所謂的「新住民」,縱使她逃回了越南,我仍然混雜著臺灣與越南的血脈。
我是所謂的「新二代」,這不是標籤,這是流淌在我血液裡的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