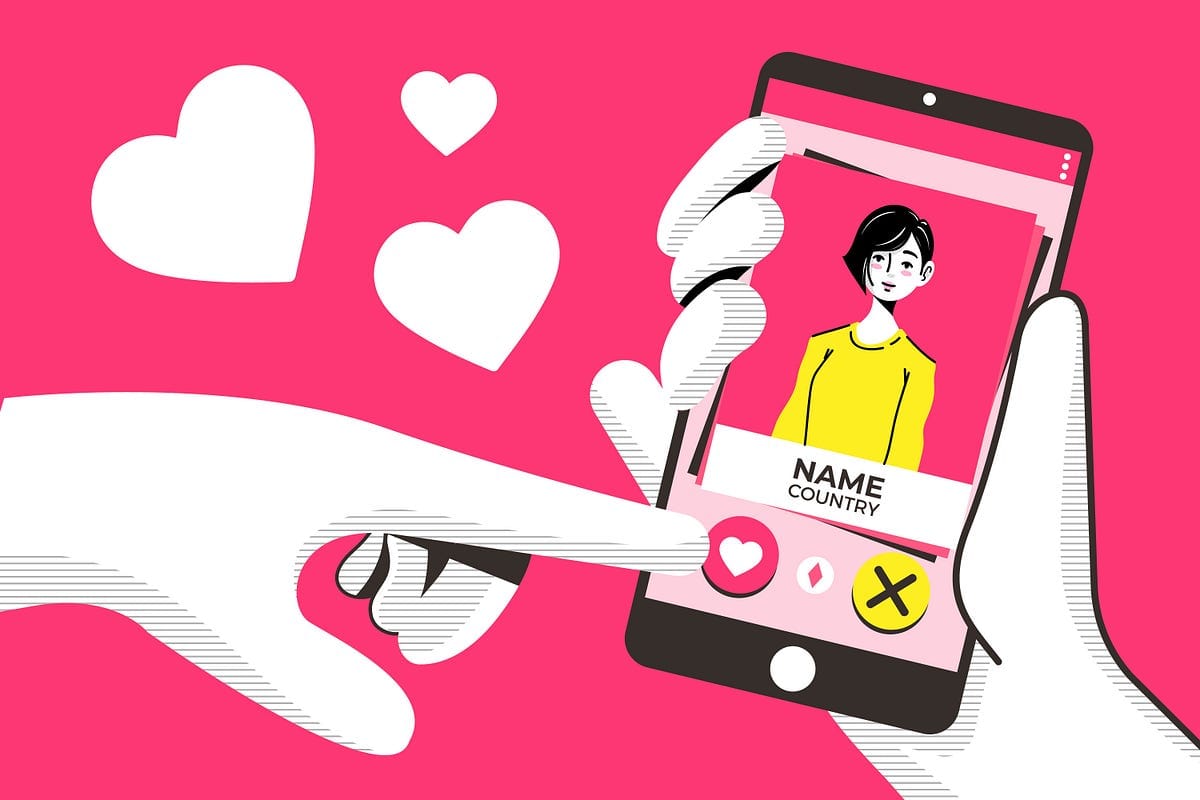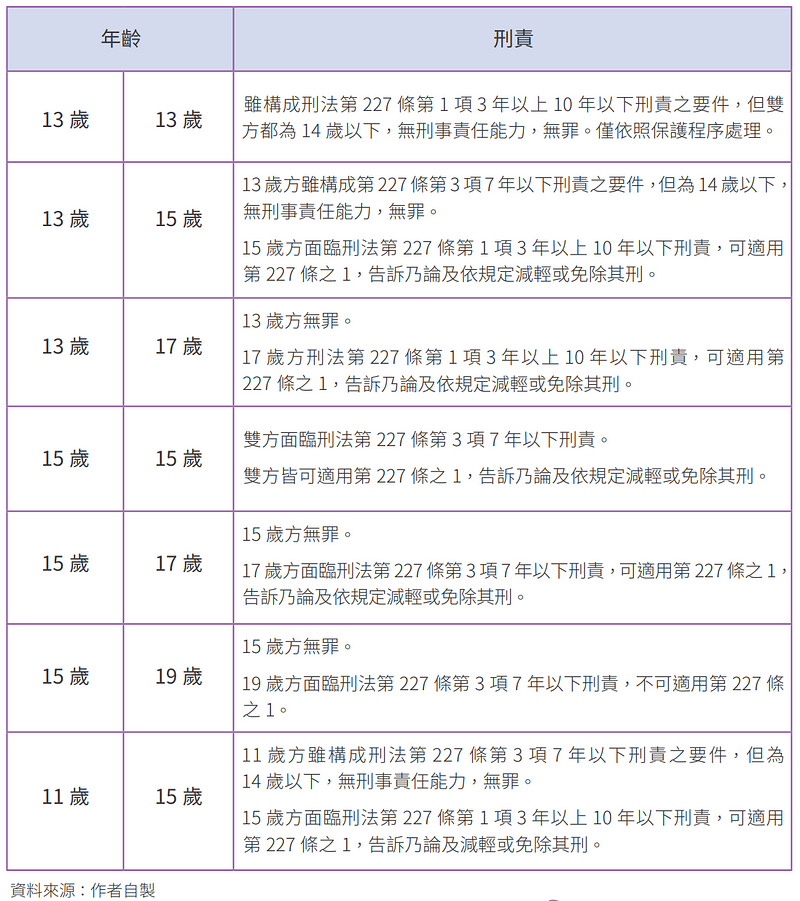專題企畫 /「媽」的力為校苦力: 多元家庭與家長的子女學校教育參與
胡郁盈│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
在臺灣近幾年的婚姻平權社會運動中,除了同性伴侶能夠締結婚姻關係的平等權利之外,同性伴侶生育子女與成為家長的可能性,也成為社會高度關注的議題。以臺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為代表的民間團體,便在婚姻平權推動的歷程中,一再強調真正的婚姻平權,必須包含對於育有子女的同性伴侶家長親權的平等賦予。這個訴求的產生,主要來自於反對婚姻平權的陣營,屢屢以一夫一妻、一父一母才是撫養孩子最理想的家庭形式為前提,提出對於同性伴侶孕育子女與親職能力的質疑;另一方面,反對方強調「婚姻」之於異性戀伴侶關係的神聖性,因此同性伴侶的法律關係必須以其他如「伴侶」或「結合」形式訂定,若此,則必然影響同性伴侶的親權認定問題。¹ 這些相關爭議,將同性伴侶家長推到婚姻平權運動的風口浪尖上,成為大眾熱議的焦點,而同性伴侶能不能運用人工生殖技術孕育子女?同性伴侶家庭有沒有適當的親職能力養育子女?同性伴侶家長的親子關係應該以何種法律形式成立?也成為婚姻平權辯論的重點之一。
[1]例如,在 2019 年 5 月立法院針對同婚法案召開黨團協商之前,立委賴士葆領銜提出《公投第 12 案施行法》草案,立委林岱樺領銜提出《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暨公投第12 案施行法》草案,分別以「同性家屬」與「同性結合」取代「同性婚姻」,作為賦予同性伴侶關係法制化的基礎。然而,不論是「同性家屬」與「同性結合」,非生母的同性家長與孩子之間的法律關係,僅能以「約定共同監護」的方式成立,與完整的親權保障差距甚遠。也因此,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在 2019 年 5 月 8 日召開記者會,向立法委員與社會大眾訴求,唯有透過同性婚姻,才能使同性伴侶家長與子女之間的親子關係,不致落入次等公民的不平等處境,也才能確保同性伴侶成家的平等權利。
雖然婚姻平權運動高度提升了同性伴侶家長的社會能見度,然而,早在婚姻平權運動之前十數年,同性伴侶家長就已經形成社群與支持團體,彼此交流生育與教養經驗。 根據何思瑩 (2008,2014) 針對女同志家長的先驅研究,過去「女同志媽媽」身分通常預設異性戀婚姻歷史,不僅在主流社會不受理解,也難以進入同志社群網絡,獲得社群資源的支持與協助;然而 2005 年開始,「女同志媽媽聯盟」成立 MSN 社群,並在隔年發行《拉媽報》,以網路社群與電子報的方式傳播女同志自助滴精的受孕技術,而在社群建 立與知識技術傳播的過程中,集體的母職渴望也逐漸成型。近年來,臺灣女同志社群進入了海外人工生殖時期,許多女同志媽媽主動在網路上分享自身經驗,編譯不同國家的精子 銀行網站頁面的英文資訊,大幅增進前往國外進行人工生殖與試管嬰兒的親近性與便利性。然而,跨國人工生殖使得醫療科技高度介入受孕方式,以及跨國生殖旅行因醫療服務商品化、國界管控、語言障礙而產生的諸多問題,也對同性伴侶家長帶來較高的文化經濟成本與健康風險 ( 孫佳婷,2017)。
由上可知,不論法律如何訂定,社會如何爭辯,同性伴侶家長與其子女的存在是既成的社會事實,而同性伴侶家長在生育與撫養孩子的過程中,則必須付出比異性戀伴侶 更多的心力與更高的代價。然而,由於社會的不理解,以及反同團體的污名化,行政院在 2019 年苦心造詣並通過的《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 以下簡稱《七四八施行法》) 為了弭平社會對立,折衷雙方訴求,雖然在關於同性伴侶結婚、離婚、繼承等相關規範,都直接準用《民法》,與異性戀配偶適用的規定無異,但在同性配偶共同生育與撫 養子女的權利與親權認定方式方面,《七四八施行法》與《民法》婚姻卻形成了不可忽視 的重要區隔。根據《七四八施行法》的第 20 條明文規定,「第二條關係雙方當事人之一 方收養他方之親生子女時,準用民法關於收養之規定。」此規定看似平凡無奇,然細究其內容卻暗藏玄機。第一、在民法與收養相關的法律條文中,從未出現被收養子女必須為 配偶一方之「親生子女」之規範;第二、加入「親生」做為必要的收養要件,將使得同性配偶無法共同收養子女,而被同性伴侶其中一人收養之兒童則永遠為法律上之單親,形 成同性伴侶的親生子女與收養子女之間重要的地位不平等。
一方面而言,若同性伴侶家長意圖建立子女與雙方家長的合法親子關係,則必須符合《七四八施行法》第 20 條的「親生」要件。然而,臺灣的人工生殖法並未因《七四八施行法》的通過而同步開放給同性伴侶使用,因此,同性伴侶家長必得透過人工生殖 一途才能生育親生子女。在這樣的法律限制之下,男同志伴侶只能通過國際代孕(意即出國到代孕合法的國家尋求代理孕母協助) 擁有親生子女;然而國際代孕受限於高昂的經濟門檻,並非一般男同志伴侶可以進行。對於女同志伴侶而言,雖然孕育親生子女的方式較多,但相對於成功率較低的自行滴精技術,現今女同志伴侶在現實條件許可之下,皆傾向以跨國或非法方式尋求人工生殖醫療技術的協助,因而必須獨自承受 承擔這些非常規的人工生殖實作所衍生的法律與醫療風險。因此,渴望擁有小孩,卻 不被允許共同收養的同性伴侶,想要在臺灣現今的法律與醫療限制中誕育自己的親生子女,一來必須擁有相當的經濟實力,才能出國求子,二來必須設法熟習法律與醫療場域的運作,才能適當地進行風險管理,而這樣以經濟與文化資本做為誕育子女的先決條件,無疑是對於有意成為家長的同志伴侶的結構性社會排除。

另一方面,無意誕育親生子女的同性伴侶家長們,在目前的法律規範之下,只能 以單身收養的方式進行非血緣子女的收養。然而,《民法》第 1075 條規定:「除夫妻共同收養外,一人不得同時為二人之養子女」,而《七四八施行法》第 20 條又只准許同性伴侶其中之一的親生子女,另一方才得進行收養。這兩條法律加乘起來的效果便是,同性伴侶只有在單身的狀態之下,其中一方才能進行無血緣子女的收養;而收養成立之後,若此同性伴侶決定締結婚姻關係,則非收養者方家長沒有任何途徑可以取 得其同性伴侶養子女的完整親權。這樣法律上的差異對待,將使得同性伴侶家長的收養子女,雖然實際上有雙親照顧,但卻在法律上將呈現永久單親的狀態。考量臺灣各項法律行政規範、福利制度、以及社會價值皆以擁有雙親作為未成年子女辦理各項業 務的預設條件²,法律差別對待之下而產生的「強迫性單親」,無疑並不符合同性伴侶 家庭收養子女的最佳利益。
[2]舉例而言,筆者的許多同性伴侶家長友人皆經歷過想要在郵局或銀行幫小孩開戶,但郵局 或銀行卻要求必須父親與母親皆到場,才能進行辦理。另外,也有同性伴侶家長想要送小孩進入有名的私立幼稚園就讀,但園方卻以家長能否陪伴小孩進行園方要求的活動作為審查標準,如此一來,擁有雙親的小孩自然比較容易達標,而單親家庭的孩子的入學資格則制度性的受到排擠。
除了法律上的差別對待而形成的各項實質社會不平等,主流社會對於理想家庭的定 義也總是囿於異性戀核心家庭的想像中,因此,同性伴侶家長教養子女的親職能力,以 及親子間的互動與和睦,也受到多方的質疑。婚姻平權的反對團體,一向以同性伴侶家長 並非一男一女,無法提供子女適當的性別角色模範,甚至可能誤導子女的性向發展為由, 反對同性伴侶生養子女。另外,2006 年桃園一件女同志聲請收養妹妹小孩的案件,雖然聲請收養人的經濟無虞,且女友以及家人皆支持收養的決定,承辦社工的評估仍認為本 案被收養人可能將會面臨到性別角色的混亂,對於被收養人將造成衝擊與困擾,而承審 法官駁回收養聲請的判決書也載明「領養小孩是當前同性戀者對於一個完整家庭之心理 或文化性期待的唯一憑藉手段,然而,兒童日後在學校及同儕間,若其性別認同,性相扮演,角色定位及社會性處境異於一般多數人,可預期的將承受極大壓力」(林昀嫺、黃詩 淳、張婉慈,2016)。由上可知,從社會大眾乃至法院,都服膺於異性戀核心家庭的規範性想像,因而在沒有確切證據的前提之下,揣測同性伴侶家長非一男一女的家庭組成形 態,將對兒童造成負面影響。
在同性伴侶家長可合法生育與領養的歐美國家,許多學術研究皆已指出,同志伴侶 家長的孩子,在身心發展的各方面與一般異性戀家庭成長的孩子並無區別;所謂缺少性 別楷模,並不會形成兒童的性別認知問題 (Adams & Light, 2015)。另一方面,若是成長於 同性伴侶家庭中的兒童,與異性戀家庭所養育之子女相比果真遭遇更多不利因素,那也 是由於負面的社會態度所致,與家長性別以及家庭形式無關(van Gelderen, Gartrell, Bos, & Hermanns, 2013)。然而,在臺灣,隱形的社會惡意與歧視,仍然固著的影響著同性伴 侶家長的育兒日常。早期的同性伴侶家長,缺少社會友善支持系統,必須單打獨鬥育兒, 而他們應對社會質疑的方式,是更加努力的做家長,做親職,要求自己與子女在各方面 都表現的比異性戀家庭更好,以此來補償同性伴侶家庭在社會眼光中的不足,向大眾證明同性伴侶家庭也可以是「適格家庭」( 曾嬿融,2013)。近年來,同性伴侶家長的親職實作,轉向強調向子女坦承本身的同志認同以及伴侶關係,並盡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現身, 以免帶給子女對於同性伴侶家庭衝突與負面的感受(潘琴威,2019)。受到婚權運動的影響,同性伴侶家長開始走上街頭,爭取平等的親權與家庭權,而社會運動的政治性,似乎也滲入了日常的親職實作中,讓出櫃與現身,成為現今同性伴侶實踐親職最重要的因素。
現今臺灣同性伴侶家長在生養子女時所面臨的種種社會與法律困境,在在顯示出異 性戀規範性 (heteronormativity) 如何將婚姻、家庭、血緣、和教養,緊緊的與二元化的 性別角色與刻板印象綁在一起。美國人類學家 Kath Weston (1991) 曾探究被排拒流放在 異性戀父權親屬體制之外的同志主體,如何經由經營伴侶關係與社群連結,建立自己的 家庭與親屬模型,並且提出「選擇家庭」(chosen family) 的概念,指出異性戀親屬體制將血緣、婚姻與家庭的連結自然化,無非是一種社會建構,而非理所當然。臺灣成功推動同性婚姻法制化,朝向解構異性戀婚家霸權邁進了一大步;然而,同性伴侶家長在現 行法律制度與社會觀念中所受到的誤解與差異對待,反映了傳統婚家觀念仍根深蒂固的存在並影響著臺灣社會的主流性別意識型態。因此,在婚姻平權的光環之下,唯有社會大眾能夠察覺、同理並消除同性伴侶家長的社會與法律不平等,才能讓臺灣引以為傲的民主與平等價值獲得更完整,更確切的落實。

參考文獻
-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2019 年05 月22 日)。
- 民法(2019 年 06 月 19 日)。
- 何思瑩(2008)。酷兒再生產:女同志的親職實作、生殖科技使用與情感認同(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北市。
- 何思瑩(2014)。「非法」情境下的酷兒生殖──台灣女同志的人工生殖科技實作。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5, 53–122。
- 林昀嫺、黃詩淳、張婉慈(2016)。同性伴侶法制實施之社會影響與立法建議。法務部委託之研究案。臺北市:法務部。2020 年10 月22 日,取自:https://civilpartnership2016.wordpress.com/
- 孫佳婷(2017)。全球化下生殖旅遊現況與評析。台灣公共衛生雜誌,36(2),95–106。
- 曾嬿融(2013)。女同志家庭親職實作(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北市。
- 潘琴威(2019)。打造同志家庭:女同志家長如何協助子女建立家庭認同。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5,59–91。
- Adams, J. and Light, R. (2015). Scientific consensus, the law, and same sex parenting outcomes.Social Science Research, 53, 300–310.
- van Gelderen, L.V., Gartrell, N. N., Bos,H. M. W., & Hermanns, J. M. A. (2013). Stigmatization andpromotive factors in relation to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adolescents inplanned lesbian 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4, 809–827.
- Weston, K. (1991). Families we choose: Lesbians, gays, kinship.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