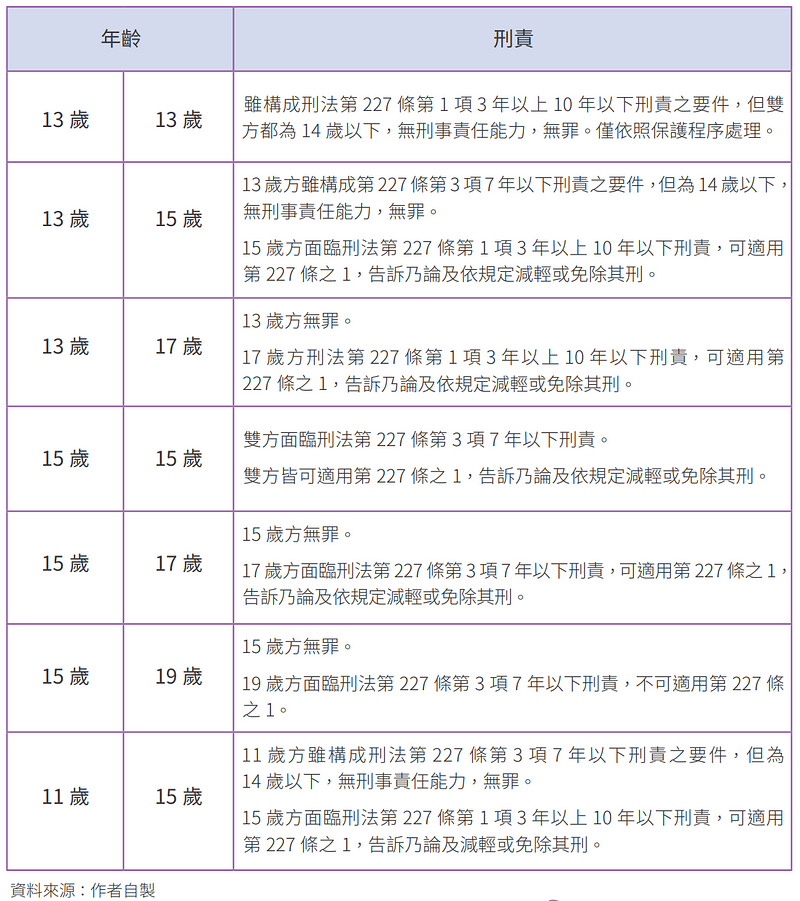性別新知 Ⅲ / 性少數的生活場景
陳庭楷 /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社會服務部社工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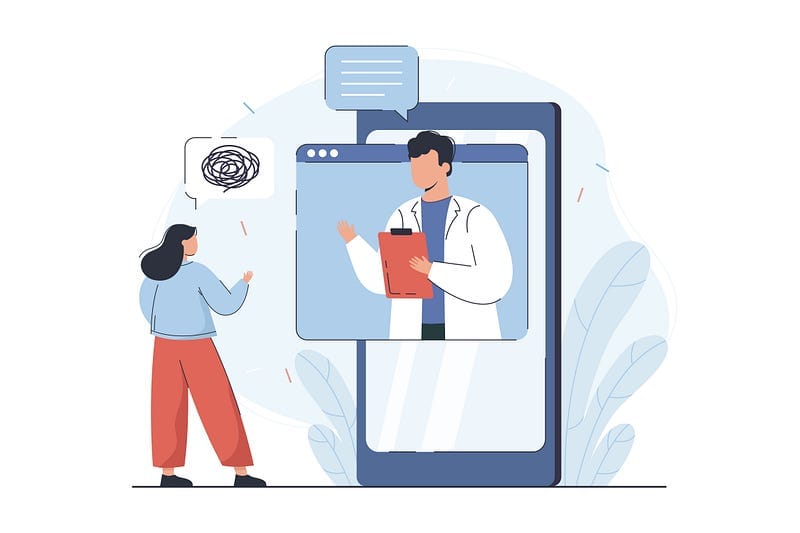
過往同性伴侶礙於不具法規範,即便為親密關係重要他人,亦僅能成為個案之「關係人」。在筆者臨床經驗之中,常見個案須進行手術及具有風險因素之醫療決策及判斷時,因關係人非為直、旁系血親屬抑或配偶,不具法律適格致無法替伴侶做任何重大醫療決策;即便醫療團隊知悉主要照顧者及重要他人皆為伴侶,但仍受限於法令限制,只能請其他家屬到場簽名或參與醫療決策,而身為個案的同性伴侶則什麼身分都不是,僅能透過「我是他的好朋友。」、「我們只是認識的朋友……」之說辭,在醫療場域隱晦地現身。
筆者於臨床實務工作以及同事經驗當中,時常面臨同性伴侶彼此陪伴以及共同參與醫療重大決策的歷程,總是會遭遇諸多困境。因此,筆者將談談自身陪伴性少數伴侶共同工作的處遇經驗,並且試著討論:「醫療決策的歷程可能會發生哪些困境?與性少數伴侶將遭受哪些情境上的困難?」
性少數身分的噤聲──來自公共場域的恐同污名標籤
性少數族群如何於公共場域被噤聲?
主流異性戀社會之性別意識形態即依男性(male)、女性(female)二分法,且男性須具有男性氣概(masculinity),則女性即須有陰柔氣質(femininity),倘個體生理性別與性別氣質未符合男性即陽剛、女性即陰柔之性別刻板印象,則易遭父權主流社會標籤,成為污名載體。
學者高夫曼(Erving Goffman)對污名做了進一步闡述,主流異性戀霸權意識形態下,社會大眾加諸於性少數族群之污名正當性,促使性少數族群將其內化為自我社會認同的一部分,進而形構污名身分認同。再者,GayleS. Rubin(1984)亦提及「性階層」的概念,劃分出何謂「好的」性與「壞的」性,壞的性則包含:濫交淫亂、非正常化關係、S/M、不具生殖的性、同性戀等,落於性階層最底層。性少數族群可能受到旁人質疑性別認同、質疑性別氣質、抱有戲弄心態開性別氣質玩笑、罹患性疾患……等,導致性少數族群為應對主流社會之反應而形構因應策略,壓抑且時時修正自我原有性別氣質,展演出符合主流性別意象之行為表態,以迴避潛在性別騷擾(gender harassment)及刻板印象。
性少數族群長期於公共領域被邊緣化,只好在公共領域(例如本文欲討論的醫療場域之中)採取隱匿身分及關係、善意謊言(非承諾性朋友關係)、刻意疏遠伴侶關係等行為策略,來應對充斥異性戀霸權之公共領域要脅,使得伴侶身分能不被曝光。因此,大多數病人及其伴侶僅能選擇於公共領域噤聲,服膺於主流異性戀文化,以確保行走於阻力最小的路(a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的影響
立法院於2019年5月24日正式施行《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以下簡稱《748施行法》)。本法以特別法之形式落實同志伴侶結婚與繼承之權益,規範保障同性婚姻權益,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就此,同性伴侶可依法向戶籍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締結婚姻賦予配偶之具備法效益之稱謂,讓醫療團隊對於個案的醫療決策與病情解釋能順利進行,使得性少數伴侶在於醫療決策上能受到法制保障,法律身分不再欠缺適格性,讓舊有醫療決策困境能夠迎刃而解。
筆者回憶臨床經驗,曾陪伴一對已登記結婚之女同志伴侶,大飛(匿名)罹患癌症末期,她和手足及原生家庭的關係普通,主要決策都是妻子處理,當時大飛顧慮於主流社會的觀感感受,對於自我性別認同以及自身與伴侶的關係沒有刻意提及,這也是十分自然,但是當主治醫師來到病床旁向大飛討論醫療計畫及決策決定時,考量後續擔憂大飛倘若因病情發展導致意識混亂或意識不清時,相關醫療決策務必需有具法律適格下的「家屬」代為大飛做重大決策,則一直在旁的伴侶就不得不出聲表示:「我是她的太太,我們已經辦理登記了。」醫療團隊聽聞後,隨即邀請大飛和太太共同討論醫療決策方向,並讓太太簽署相關同意書。若非法律保障,則大飛與太太的意願共識很可能又將被社會主流規範所噤聲。
身分暴露與家庭紐帶之兩難
舊有臨床工作者在面臨性少數伴侶之醫療決策,總受限於法律親屬規定,需要具有直系/旁系血親方為病人之決策人;即便病人本身恐因為性少數身分認同使得自己與原生家庭關係疏遠,且日常生活當中主要照顧陪伴者皆為伴侶,需做重大醫療決策時,陪伴在身旁的親密伴侶仍僅能形同陌生人無法參與,只能聯繫關係疏遠的親屬來替病人做出重要決策。另外,性少數伴侶能否有勇氣踏出第一步,去戶政登記結婚也是另一個問題,其背後要克服的困難眾多,雖然有法律上的保障及認可,個體仍需要擔負性少數身分曝光的間接出櫃風險(例如:身分證背後的配偶欄、戶籍謄本的異動資料)。
在筆者另一個與個案共同工作的經驗中,遇過一位個案小A,他沒有近親家人,只和小A所稱的「好朋友」一起住,生活大小事情都是雙方互相打理。在小A臨終前,曾表示想要將自己的喪禮及遺產都委託給朋友全權處理,感謝他的辛苦,惟因雙方並無任何結婚登記,囿於法規的限制,臨床上的作法仍是要透過戶政系統及里長硬找尋其「遠親」來辦理小A的喪葬事宜,但也因為這個遠親親屬關係實在是太遠了(已逾旁系血親四親等以上),對方其實根本不認識小A,故僅能簽屬委託書給公部門代為處理。原先小A臨終前遺囑想要交由「好朋友」處理的這個遺願,則無法圓滿地達成,讓筆者深感惋惜,產生了一種明明是最親近的人卻無法代為決定及處理,反而要聯繫平常沒有往來、如同外人的親屬來行醫療決策。
即便《748施行法》已正式實施,仍然存有其他潛在問題:對於未向家人出櫃的性少數伴侶來說,當欲行重大醫療決策時,除非病人與原生家庭關係惡劣否則逕由配偶決策即可,但當面臨病人本身與原生家庭關係良好,可是尚未向家人出櫃之情況,面對病人本身的相關醫療決策,多仍聯繫原生家庭決策為主,使得性少數配偶縱使具有法規範予以保護,伴侶仍必須自我邊緣化角色,抑或讓原生家庭知道雙方已締結婚姻(出櫃),方能進入共同決策的核心,進而使得性少數伴侶落於身分暴露與家庭親情紐帶之間的兩難抉擇。
潛在的紛爭風險:繼承
即便是已經締結婚姻之性少數伴侶,無論與原生家庭關係緊密或疏離、無論同志伴侶關係出櫃與否,面對重大醫療決策,將會影響到病人主體後續醫療計畫、病況發展等走向與決定。筆者擔任社工師以來,最為常見的紛爭總是出現在病人過世後,因為涉及病人遺產繼承事宜,導致排列於優先繼承順位家屬開始發難。
性少數伴侶雖擁有婚姻上的法律保障,配偶係第一優先繼承序位,但是對於尚未出櫃的伴侶來說,即便法律賦予其繼承權,惟在主流父權體制文化及意識形態運作之下,原生家庭仍將以(異性戀霸權的)約定俗成繼承,認為其原生家庭才有繼承應當權利,進而對於遺產的繼承分配與否,造成潛在紛爭。
結語
綜觀上述,筆者的社會工作實務經驗當中,即便性少數伴侶已受到《748施行法》保障,但在實際生活經驗、醫療決策與陪伴的過程中,仍有許多需要看不見的困境。社會文化背後仍存在著難以鬆動的多重結構,譬如社會文化層面、政策面、法律面,使得性少數伴侶至今仍持續落於被邊緣化、污名化的社會處境。
前述小A的例子亦讓筆者進一步省思,現代社會家庭組成型態越發多樣,也存在著不具血親關係所組成的家庭,需要其他相關法案的推動,以保障現代社會多元家庭樣貌。
期許多元性別友善的現代,經由權益倡導、性別教育、法制改革之方式讓性別意識融入大眾的生活、進入到社會大眾的視野內,讓社會環境結構能越發友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