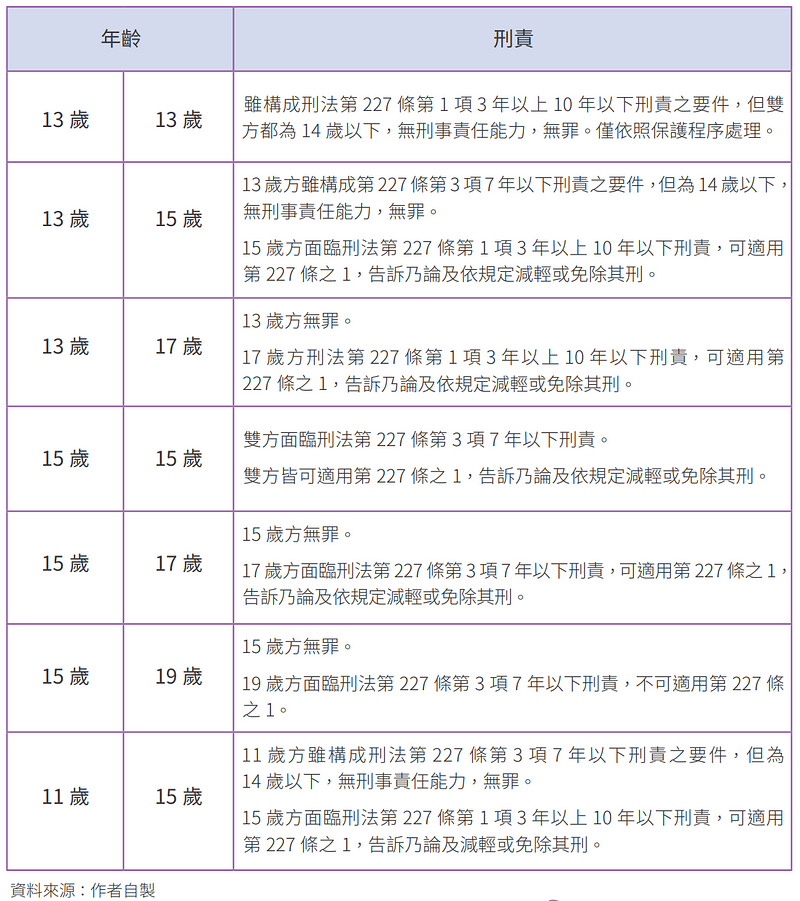專題企劃 / 姓氏的性別政治
陳昭如/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特聘教授、Hauser Global Professor, 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一、父姓常規的現實
2007年,內政部首度公布子女從姓的統計,印證了人們對臺灣社會從父姓現象的常識:全臺灣的人口中,僅有約1.93%的人從母姓(內政部,2007,頁213)¹。就在這一年,規範子女姓氏的法律制度也有了驚天動地的變化,立法院通過修正民法親屬編第1059條、新增第1059–1條,承認父母有約定子女姓氏的自由、個人有決定從父或母姓的自由。新法廢除子女應從父姓、僅在母無兄弟時才能例外約定從母姓的舊規定,改為由父母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從母姓,並且規定在符合特定條件的情況下,允許父母為子女改姓、子女在成年後改姓²。15年之後,根據內政部2022年1月的統計,在所有新生兒中,從母姓者已有5.22%,但由父母雙方約定從母姓者僅有2.78%(其他主要為非婚生子女從母姓)³。相較於剛修法通過的2008年有1.78%的父母約定子女從母姓,2022年的父母約定從母姓比例僅成長了1%。
[1]比例係筆者自行計算。該統計所使用的說明是「同母姓」,其意義較「從母姓」精確,因其同時包含父母同姓的狀況。不過,為表達「從姓」的權力關係,且同姓狀況比例甚低,因此本文以「從母姓」表述之。
[2]在2007年修法後,立法院曾於2010年再度修法,增訂父母無約定時以抽籤定之的規定(原規定於戶籍法第49條第1項前段),將子女改姓的規定由「對子女有不利影響」改為「為子女利益」,並刪除了成年子女改姓仍需父母書面同意的要件。
[3]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民法修正施行後登記子女從姓案件統計表)
在子女姓氏法律改革之後,父母獲得了約定子女姓氏的自由,不再被法律要求必須讓子女從父姓,自由約定的契約模式取代了應從父姓的強制模式。一個弔詭的現象於是誕生:原為改革父姓常規的契約模式,卻賦予父姓常規新的正當性基礎,因為從父姓是由來於人們的自願選擇,而不是法律強制的結果。於是,以「約定」取代「強制」、「性別中立」取代「男性優先」的法律改革沒有廢除父姓常規,反而將之正當化了。
在性別中立的契約模式之下,為何絕大多數的父母仍「選擇」約定子女從父姓,因而使得子女從姓的狀況在契約模式與強制模式無甚差別?這似乎不是因為人們對於父姓常規堅定不變的擁護態度。因為,從中研院社會變遷調查的結果來看,人們對於子女從父姓的支持態度在近年來已較為弱化、對從母姓的支持態度也已增強,2012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7成的民眾同意在有些情況下可以讓子女從母姓,且其中有近半數表示願意讓自己的子女從母姓⁴。顯然,人們對於子女姓氏漸趨開放的態度和意願並未轉化為命名的行動與現實。
[4]依據2012年中央研究院「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六期第三次調查,僅有27.8%的受訪者認為子女一定要從父姓,70.1%的受訪者認為在有些情況下可以讓子女從母姓,且在這些同意子女可以從母姓的受訪者中,有48%的人表示會讓自己的小孩從母姓(章英華、杜素豪、廖培珊,2013,頁302)。相較之下,2002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四期第三次的結果,僅有21.79%的民眾贊成子女從母姓,只有13.72%的民眾願意讓自己的小孩從母姓,且贊成子女從母姓的人們只有半數願意讓自己的小孩從母姓(章英華、傅仰止,2003,頁329)。不過,依據「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1990年到2010年的調查結果,支持從父姓的比例由1990年的85.2%降到2010年的62.9%,而認為從父或母皆可的比例則由12.9%上升至35.8%,但支持小孩從母姓的比例始終不到1%。(資料來源:http://www2.ios.sinica.edu.tw/TSCpedia/index.php/您認為小孩的姓應該怎麼安排?)。
如果人們支持父姓常規的態度不足以完全解釋契約模式難以改變現實的窘境,有什麼其他的解釋可能呢?在思考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可以先比較夫妻冠姓的契約制度。妻冠夫姓的制度曾經是臺灣社會的常規。在新女性主義運動昂揚挑戰父權社會的1970年代,呂秀蓮曾經質問:「女孩子結婚久了,只聽得左鄰右社親朋戚友喊她某太太,自己姓甚名誰差點給忘了,從娘胎裡走出來的小生命,竟也一個都不記他娘的帳!」(呂秀蓮,1974,頁50)。她所批評的是女人從夫、為男人生育小孩的冠夫姓與從父姓現象。當時的民法第1000條規定,妻應冠夫姓,但得例外約定不冠姓。解嚴後,在女性主義法律改革運動的推動下,1998年修法廢除了妻應冠夫姓的原則性規定,改為夫妻原則不冠姓,得例外約定冠配偶姓。今日,雖然冠姓者多為冠夫姓,但已經鮮少有夫妻約定冠配偶姓⁵。而且,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登記結婚的同性伴侶不適用配偶冠姓的規定,更進一步在同性婚姻制度中取消以姓氏表彰雙方婚姻關係的可能⁶。
[5]依據2018年的統計,全國約111萬冠配偶姓的人口大多數為60歲以上,且總計僅有1882位是男性,其中未滿50歲者僅有78位(內政部,2018,頁202)。而且,撤銷冠姓的人遠多於約定冠配偶姓的人(內政部,2018,頁73)。
[6]因此,我們無法藉由觀察婚姻姓氏約定權在「第二條關係」的實踐來了解同性伴侶關係的平等意涵究竟是合法化同性婚姻會創造新的婚姻姓氏平等實踐(合法化同性婚姻可以改變異性戀父權婚姻的不平等),或者會實踐出新的不平等(異性戀父權婚姻會「同化」同性關係)?例如,英國與澳洲的研究都顯示,同性伴侶相較於異性伴侶在婚姻姓氏的選擇上有較平等多元的實踐(Patterson & Farr, 2017; Dempsey & Lindsay, 2018)。
同樣經歷了以契約模式取代強制模式的法律制度變遷,冠夫姓的現象已幾近消失,但從父姓的現象卻僅有輕微的鬆動。為何約定權可以促成妻子的姓氏獨立,卻難以有助於傳承母姓?這是個鮮少被提出的經驗謎題。回答這個謎題有助於我們思考改變父姓常規為何如此困難、又如何可能。以下,我將先探究冠夫姓與從父姓現象的經驗謎題,再提出創造改變的可能方案。
二、冠夫姓與從父姓現象的經驗謎題:契約模式的作用為何有別?
1998年民法親屬編修正,將妻應冠夫姓、例外得約定不冠姓的規定改為夫妻得約定冠配偶姓⁷。根據推估,1960年代有過半數的女性結婚冠夫姓,但在修法時的1990年代後期臺灣社會,結婚冠夫姓僅佔當時已婚或曾有婚姻經驗的女性的1%而已(Chen, 2018, p.58),可見修法當時臺灣社會的冠夫姓文化已有了相當大的變化。2007年民法親屬編修正同樣採取契約模式,廢除子女應從父姓、母無兄弟時得例外的規定,改為由父母約定從父或母之姓。在修法之時,從父姓是常態,且持續至今日仍以從父姓為主流。
[7]舊民法第1000條除規定妻應冠夫姓外,也規定贅夫應冠妻姓,但皆得例外約定不冠姓。舊民法第1059條也規定招贅婚的子女從母姓。1998年的修法廢除了招贅婚。本文不另討論招贅婚的相關規定。有關招贅婚與從母姓的關係(規範緣由、將嫁娶婚改為招贅婚作為從母姓的策略),可參考陳昭如(2014,頁292-93, 295-97)。
如此來看,冠夫姓與從父姓的兩個契約模式法律改革有個巨大的背景差異:在修改冠夫姓法律時,已婚女性約定不冠夫姓、維持婚前姓氏已成常態,法律的改變反映了社會已經發生的變化;但在修改從父姓法律時,社會仍以從父姓為常態。考量此背景差異來回答前述的約定權經驗謎題,很容易會得出「鏡像論」(the mirror thesis)的解釋:廢除妻應冠夫姓的修法反映了已經存在的社會變遷,法律隨著社會變遷而改變,法律變遷是社會變遷的產物;廢除子女應從父姓的修法是鏡像論的例外,其結果說明了以法律來改變社會、創造社會變遷的有限性。
然而,鏡像論的「法律反映社會」命題其實無法有效解釋此經驗謎題,因為冠夫姓與從父姓傳統的歷史不同,規範方式不同,法律與社會互動的動態更有別(Chen, 2018, pp.36–40)。首先,子女從父姓是淵遠流長的漢人傳統,但妻子冠夫姓的傳統卻是相對晚近的產物。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初期,冠夫姓的現象並不普遍,即便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建立戶口制度並以行政命令要求冠夫姓之後,此現象仍不普遍,直到皇民化之後要求已婚女人「改為夫姓」才出現普遍改夫姓的狀況,但為時不長(魏世萍,2002)。換言之,冠夫姓是被殖民者所發明的「傳統」。
1945年,日本結束在臺灣的殖民統治,新的統治者在臺灣施行中華民國民法,自此才有法律明文規定妻應冠夫姓、例外得約定不冠姓。然而,早在1950年代就有菁英女性許世賢因爲參政考量而撤銷冠夫姓(從「張許世賢」改為許世賢),到了1960、1970年代之後,更因女性受教育與勞動參與的顯著增加、新女性主義運動的倡議,已婚女性因為冠夫姓而造成的社會生活不便(如:證件或學歷上的姓名不同、在職場上使用的姓氏改變)與政治參與障礙(如:投票名冊上的姓名不同)等因素而受到社會關注,廢除冠夫姓的規定甚且成為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期被討論的民法修正草案內容,只是最後未能在立法院獲得通過(Chen, 2018, pp.11–31)。由此可見,冠夫姓不僅是近代被法律所創造的產物,更是根基不穩的「新傳統」。相較之下,子女從父姓的「舊傳統」雖然同樣在1945年才成為法律的明文規定,但其歷史更為悠久、也更為根深蒂固。
其次,我們必須留意夫妻冠姓與子女從姓規範的差異,以及法律與社會互動的不同。夫妻冠姓的舊法規定是以「冠姓」為預設規則(default rule),以「不冠姓」為例外規則(exceptionrule),允許人們可以「選擇退出」(opt out)。自法律實施以來,行政機關就沒有偏好預設規則,相反地,行政機關經常要求公務員應該尊重夫妻雙方的協議、不得強迫冠夫姓,並且對於撤銷冠姓採取寬鬆容許的管制態度。在這種「契約先行」的管制下,有不少女性能夠取得丈夫的同意不冠夫姓,於是使得「法律上的例外」(de jure exception)成為「事實上的預設」(de facto default)(不冠姓),「法律上的預設」(de jure default)成為「事實上的例外」(de facto exception)(冠姓)。在1998年修法之後,法律上的預設規則是「不冠姓」,例外規則是性別中立的約定冠姓,也就是夫妻要冠姓必須「選擇採用」(op tin)、夫或妻皆得約定冠配偶姓,不想冠姓者不需要另外動用約定權,且既然妻子不冠姓已經成為事實上的預設狀態,夫冠妻姓又是一種少為人所實踐的、違反性別常軌的安排,「法律上的預設」便與「事實上的預設」相符。相較之下,子女從姓的舊法規定是以「從父姓」為預設規則,但無約定從母姓的例外規則(1985年之前)或僅有嚴格的從母姓例外約定規則(1985年後至2007年修法前,必須滿足母無兄弟的條件),而且行政機關並不積極回應人們訴諸例外規則以讓子女從母姓的「行政動員」(陳昭如,2014,頁293–301,327–329)。因此,有別於不冠夫姓的例外規定成為事實上的預設狀態,約定從母姓的法律上例外規定同時也是事實上的例外狀態。在2007年修法後,父母雙方共同約定子女從姓成為法律上的預設規則,父姓常規藉由人們的約定而成為預設規則的實踐,而例外抽籤的規定是在雙方約定不成的情況下才能適用,想違反父姓常規、又無法取得對方同意的母親,必須堅持反對至協議不成的程度才能適用抽籤的例外規定,事實上也僅有非常少數的人使用抽籤的方式決定⁸。因此,已婚女性大多維持本姓的現象並非「與法無關」的社會變遷自然形成,而是人們與法律互動的結果;子女大多從父姓的現象並非「與法無關」的社會文化傳統,也同樣是人們與法律互動所形成。兩者的預設與例外規則不同,影響了社會與法律互動的樣貌與結果。
[8]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民法修正施行後登記子女從姓案件統計表)。抽籤的結果多為從母姓,一般推測這可能是重複抽籤的結果。
再者,我們也必須留意「改姓」與「決定出生姓氏」的不同,出生姓氏會產生「定錨效應」(anchoring effects),人的姓名自我認同與外部承認因著歲月的增長而日益穩固,而且改變原有姓氏的行政與社會成本(更換證件、改姓前的文件效力等等)不利於改姓,因而使得一個人出生後所被給予的姓氏隨其成長有定著化的效果,出生姓氏通常就是一輩子的姓氏。本專題的作者之一師彥方的改姓時點考量(她為何選擇在從事律師工作之前改姓),就說明了定錨效應對於改姓決定的影響。定錨效應有利於女性「鎖定」出生的姓氏、在婚後保留本姓,因此1998年修法之前的已婚女性可以藉由例外約定權來退出冠夫姓的預設規則,在修法之後也鮮少利用例外約定權來冠夫姓。相對地,定錨效應無助於母親行使子女姓氏約定權,反而會鞏固父母在子女出生後的姓氏契約,使其更難在日後被變更,因而固著化從父姓的約定。根據官方統計,改姓的人數並不多,而且改從父姓的人數遠多於改從母姓的人數,被認領的人更有8成以上與生父同姓⁹(內政部,2018,頁73、222),這很可能與母姓的非婚生污名¹⁰有關。因此,父姓常規之強大表現於父姓較能產生定錨效應,也較能打破子女出生從母姓的母姓定錨效應。
[9]依據現行民法第 1059-1 的規定,非婚生子女從母姓,經生父認領後,雙方得約定變更姓氏。因此,內政部的統計可解釋為:原從母姓的非婚生子女,在被生父認領之後,有8成改為從父姓。
[10]在不同國家法律與社會脈絡下,母姓不一定有非婚生污名。以美國為例,由於多數已婚女性改為夫姓,子女與母親異姓才會遭受私生子污名,而女性保留婚前姓也因此容易讓小孩被誤認為私生子。有些已婚女人改為夫姓的理由就是不希望小孩被認為是私生子(Kim, 2001, p.931)。黑人女性主義法學者 Melissa Murray 就曾經描述一段與朋友的對話,她的朋友質疑她保留婚前姓的決定,認為這容易讓她的小孩被誤認為私生子(Murray, 2011, p.388)。
夫姓易移,母姓難從的結果是:維持本姓的母親往往成為家中唯一的「異姓人」 — — 父親與小孩同姓,只有母親不同姓,而異姓象徵了母親的外人身分。以契約模式規範夫妻冠姓與子女從姓的法律維持了兩種現狀:「不冠姓」與「從父姓」的現狀。性別中立的契約模式有助於維持現狀,因為這樣的模式極小化對現實的干預,尊重「不受干預的自由」。既然夫妻冠姓的法律規則已改變為預設不冠姓,且在前述法律與社會互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不冠姓的實踐,不干預的契約模式就維持了不冠姓的現狀,約定冠姓成為例外。然而,子女姓氏的法律規則是預設父母的契約自由,但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中,契約自由往往對現實上的強者有利 — — 試想,雇主和勞工,誰享有比較大的契約自由? — — 在現實上佔據優勢地位的父姓就很容易獲得母親的「同意」,而較為優勢的女性則可能享有較大的協商權。研究顯示,教育和職業上較為優勢的女性不僅較支持子女從母姓,也比較有可能獲得丈夫支持(Chenetal., 2017)。
依據中央研究院「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於2012年調查的結果,人們支持子女從父姓的最主要理由是「一般都這樣」,而支持從母姓的最主要理由則是認為只要父母約定就可以(章英華等,2013,頁302)。這正說明了父姓的支持者不一定是有意識地進行了價值判斷,可能是無意識地依循常規;而從母姓的支持者則多肯定自由約定的價值,但即便肯定約定自由的從母姓支持者,也不見得能將其意願轉化為現實上的約定,因為雙方協商的權力與結構往往並不對等。而且,在多數狀況下,法律所規定的「約定」沒有經過真正的協商過程,而很可能只是在制式的書面同意書上簽字。依據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於2019年所進行的法文化與社會變遷調查結果,有近9成的父母在決定小孩姓氏時沒有經過討論,僅有4.5%的父母曾仔細討論¹¹。於是,被正當化的強制成為同意(coercion legitimated becomes consent)(MacKinnon, 1989, p.238),契約並未終結父權,而是成為父權現代形式的鞏固(Pateman, 1988,p.187)。常規的慣行需要積極的措施來促成改變,而契約難以扮演積極改變現狀的角色。
[11]http://tadels.law.ntu.edu.tw/database-society/2019-臺灣法文化與社會變遷調查第五期/。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同一個調查,6成的人們在簽訂手機通訊合約時會大致瀏覽契約內容,但也僅有7.2%會仔細審閱。手機通訊合約與子女姓氏契約這兩種契約都可能涉及雙方締約地位不對等(業者vs.消費者,父vs.母),而人們大概都會同意,後者較前者重要,後者卻往往沒有經過討論過程,而前者的內容至少會被大致瀏覽。
前述的批評並非要指責那些同意子女從父姓的母親是被傳統父權擺佈的棋子、是無意識或有意識支持父姓常規的父權受害者。從母姓的選擇或許也可能是Qi Xiaoying(2017)在探討中國一胎化政策與母姓傳承時所稱的「隱晦父權」(veiled patriarchy)(母姓傳承的性別策略弔詭地強化了父權),也可能是Deniz Kandiyoti(1988)所稱的「父權協商」(bargaining with patriarchy):女人在受限的條件下藉由策略化地配合父權規範來獲得特定利益,但此種策略性配合維繫了父權結構,而非挑戰之。有一個澳洲研究便指出,女性是因為對自己與子女有利而選擇配合父姓安排(Dempsey& Lindsay,2018)。這可能也是臺灣女性選擇子女從父姓的性別策略。
三、改變如何可能
在社會與法律的互動下,尊重雙方自主的契約模式運作結果是:夫姓易移,母姓難從。對契約模式的反省能夠帶來何種改變父姓常規的出路?驕傲從母姓運動(彭渰雯,2016)這類的社會倡議是重要的,去除從母姓的污名、增強女性締約意願與能力的倡議是創造社會改變所不可或缺的行動。但法律改革與社會倡議並不衝突,二者可以、也必須並肩而行。
在鄰國的日韓,父姓常規與家制度的糾結持續維繫了男性中心的家戶制。韓國民法原則從父姓、例外得約定從母姓的規定持續造成男性中心的歧視與母系的空洞化(Yang, 2018),而日本民法以雙方約定決定「家姓」的規定被最高法院認定合憲,即便最高法院明確認知到96%的家庭是以丈夫之姓為家姓而造成多由女性承受改為夫姓的不利益,仍然表示已婚女性使用「通稱」就可以緩解此不利益(Ishida, 2018),而且最高法院在2021年又再度認定夫妻不得別姓的規定合憲。這顯示契約的約定制度 — — 韓國性別特定的例外約定從母姓,日本性別中立的約定家姓,臺灣性別中立的約定子女姓氏 — — 難以撼動父姓常規的窘境。在韓國的脈絡下,梁鉉娥主張修法規定由父母雙方約定子女姓氏,調和個人選擇理論和女性主義的傳統發明,促成姓氏意義由父權傳統定義的父系傳承轉變為個人認同的變遷(Yang, 2018)¹²。不過,臺灣10餘年的經驗顯示,雙方約定的契約模式作用非常有限。如此一來,創造改變的法律選項何在?司法訴訟固然是一個選項,但以我國大法官對於性別平等所採取的形式平等取徑來看,要在司法上挑戰性別中立的法律,恐怕難以成功,雖然失敗的司法訴訟仍可以產生社會運動的意義。
[12]石田京子則認為應以公眾教育來促成修法的變革(Ishida, 2018)。
就立法與行政改革途徑來看,Elizabeth F. Emens(2007)對於美國姓氏改革所提出的建議值得參考。在美國,即便經歷了1970年代各州的法律改革,女性改從夫姓(從而子女也會從父姓)已非法律上的強制規定,卻仍是多數人們的實踐。Emens建議透過一系列規則的改造,在保留姓氏選擇權的同時讓人們得以透過選擇權來改變常規,這包括:
(1)改變「預設規則」(default rules),例如讓預設規則有助於促進改變,亦即設計有利於改變的預設(facilitating default),或者採取「基進」的預設(radical default);
(2)修正「改變規則」(altering rules),改革例外規定,也就是當事人可以用契約來回應預設規則的規則;
(3)創造一組「構框規則」(framing rules),包括提問性、資訊性與提問脈絡的構框。Emens認為,「櫃檯公務員法」(desk-clerk law:“what the person at the desk tells you the law is,”亦即由櫃檯服務的公務員告知民眾的法)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可以透過改變「櫃檯公務員法」來促成變革。
改變臺灣父姓常規的法律與行政改革,可以考慮改革前述三種規則(Chen, 2018, pp.53–54),例如:
(1)改變「預設規則」,改採「隨機決定優先」的促進性預設規則(降低協商成本且不偏好任何一方)¹³,以「抽籤」為預設規則;或者改採「原則從母姓」的基進預設規則。開放使用第三姓,更可以打破從母姓=從母之父姓的雙重困境(Leissner, 1998)或「姓氏的兩難」(Lebell, 1988)。此外,廢除婚生與非婚生的區分,也可以緩解母姓的非婚生污名。
[13] Emens 所提出的隨機方案就包括擲硬幣、電腦抽籤。
(2)變更「改變規則」,放寬並多元化改變規則,例如允許第三姓、以「主要照顧者」的親權行使原則來讓主要照顧者享有較大的決定權。此外,考量到姓氏的定錨效應,也可以多元化改變規則的時間點,放寬改姓的次數限制,考量政府與學校機關在入學、申請領取身分證或其他證件、成年等時間點,主動提供更改姓名的機會,並且讓換發載有姓名的證件更為容易。
(3)改變「構框規則」:以「不預設從父」、「主動告知」等構框規則來改變「櫃檯公務員法」,讓戶政事務所的公務員在受理姓氏登記與變更時,可以用更積極的作為來主動提供資訊、正面回應,促進父母的實質協商、並考量不遵循性別常規的可能性。
消極不干預、尊重父母自主的契約模式支持「無干預的自由」,這對於父姓難移、母姓難從的困境作用有限。要改變現狀,撼動父姓常規,需要更積極的法律措施,以創造「無宰制的自由」。
消極不干預、尊重父母自主的契約模式支持「無干預的自由」,這對於父姓難移、母姓難從的困境作用有限。要改變現狀,撼動父姓常規,需要更積極的法律措施,以創造「無宰制的自由」。
參考文獻
內政部(2007)。全國姓氏要覽。
內政部(2018)。全國姓名統計分析。
呂秀蓮(1974)。新女性主義。幼獅。
章英華、杜素豪、廖培珊(主編)(2013)。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六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
章英華、傅仰止(主編)(2003)。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四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
陳昭如(2014)。父姓的常規,母姓的權利:子女姓氏修法改革的法社會學考察。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43(2), 271–380。
彭渰雯主編 (2016)。歡喜從母姓。女書文化。
魏世萍(2002)。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對臺灣漢族已婚婦女姓氏之規範。臺灣史料研究,18,75–87。
Chen, C., Peng, Y., & Chang, C. (2017). Women’s (No) Naming Right under the Shadow of patronymy: Changes of the public attitudes in Taiwan between 2002 and 2012.Survey Research — Method and Application, 38, 57–97.
Chen, C. (2018). Becoming “Outsiders Within”: A feminist social-legal study of surname inequality as sex, race, and marital status discrimin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Korean Law, 18, 1–58.
Dempsey, D. & Lindsay, J. (2018). Surnaming children born to lesbian and heterosexual couples: Displaying family legitimacy to diverse audiences. Sociology, 52(5), 1017–1034.
Emens, E. F. (2007). Changing name changing: Framing rules and the future of marital nam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74(3), 761–863.
Ishida, K. (2018). Why does surname matte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rospect of family law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in Japan. Journal of Korean Law, 18(1), 59–82.
Kandiyoti, D. (1988). Bargaining with Patriarchy. Gender and Society, 2(3), 274–290.
Kim, S. A. (2001). Marital naming/Naming marriage: Language and status in family law. Indiana Law Journal, 85(3), 893–953.
Lebell, S. M. G. (1988). Naming ourselves, naming our children: Resolving the last name dilemma. Crossing Press.
Leissner, O. M. (1998). 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 Cardozo Women’s Law Journal, 4(2), 321–407.
MacKinnon, C. A. (1989).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urray, M. (2011). What’s so new about the new illegitimacy. Americ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Gender, Social Policy & the Law, 20(3), 387–436.
Pateman, C. (1988). The Sexual contra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atterson, C. J., & Farr, R. H. (2017). What shall we call ourselves? Last names among lesbian, gay, and heterosexual couples and their adopted children. Journal of GLBT Family Studies, 13(2), 97–113.
Qi, X. (2017). Neo-traditional child surnam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Women’s rights as veiled patriarchy. Sociology, 52(5), 1001–1016.
Yang, H. (2018). Imaginary construction of the mother’s empty blood: Patrilineal surname law in Korea and its significance. Journal of Korean Law, 18(1), 83–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