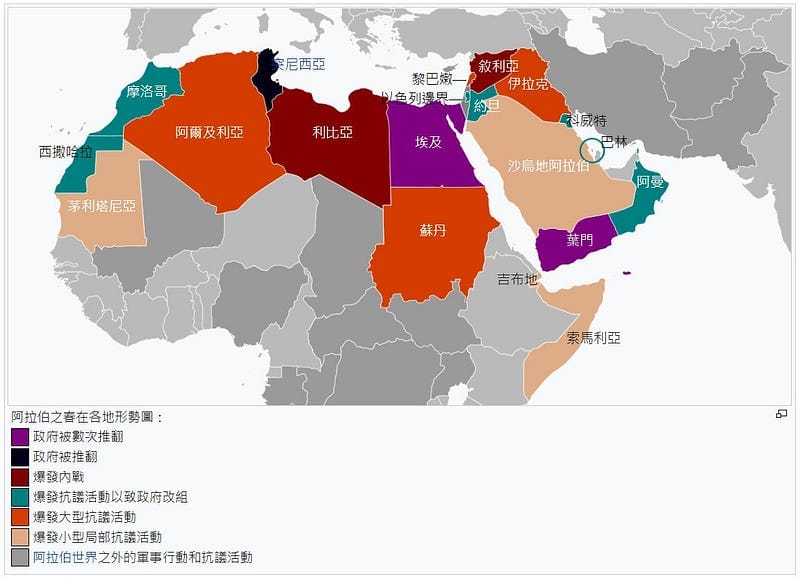特別企劃 / 新二代留聲機
廖建豪 /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大二生
關於那形構複雜的家庭與無以名狀的歉意
30年前,1992年,臺灣政府公布實施「就業服務法」,正式開放移工前往臺灣工作,而我的母親在6年之後,一如其他數以百萬計的菲律賓女性,為了支撐家庭經濟而踏上成為OFW(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菲國跨洋勞工)的道路。
母親說那是1998年,28歲的她與前任伴侶在菲律賓育有一子一女,可前任無故消失,身為單親媽媽的母親為了給孩子們更好的生活,將彼時年僅8歲與6歲的兒女託付親人照顧,並借貸了約3萬臺幣的金額支付仲介費,隻身前往臺灣工作,展開2年約期的OFW人生。怎麼也沒想到,母親這麼一去就成為了臺灣的新住民,與身為雇主的父親結了婚,並在2002年生下了我。而這個異國婚姻家庭的誕生,除了日久生情,我想也和父親與母親相似的過往有關。
父親說那是1993年,25歲的父親與前任伴侶結了婚,育有兩個女兒,可後來婚姻失和,走上離婚一途。當時的父親,一如其他3位兄弟姊妹,繼承了爺爺奶奶的衣缽,各自在不同的傳統市場賣魚維生,父親也藉此撫養兩個女兒長大。時至1998年,年邁的爺爺奶奶身體惡化,長期肩負女兒與父母照護責任的父親決定聘請移工,以減輕生活上的壓力。於是,兩個生命經驗相似的人相識,在4年後重組了家庭,而我便是在第二段婚姻當中──擁有兩個臺灣姊姊、一個菲律賓姊姊和一個菲律賓哥哥的「獨子」。
固然依血緣望去,我處在一個成員眾多的跨國婚姻重組家庭,但由於哥哥姊姊們都另有住所,且親戚們也並非同居,所以自我有意識以來,我對「家庭」組成的想像主要以父親、母親與我為主,與一般的「小家庭」差異不大。不過關於這個形構複雜的家庭背景,我其實明白,相較其他同母異父與同父異母的手足,我不曾體會過父母親長期不在身邊的日子;相反地,同樣身為父親與母親的孩子,我卻是從小獲得最多資源與關愛的那位。然而我的腦海總不時浮沉這個想法中──我好像借走了別人的父母。我想,即便明白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但於我而言,仍然難逃於一份無以名狀的歉意,而那就猶如基因般注定,流淌於我血液,形影不離。


身為一位「不負責任」的市場囡仔
母親嫁來臺灣後,便隨父親經營魚攤,為求工作方便,父親在我約莫3歲時決定在市場附近租房,而我的童年,也就這麼與其他同為市場二代的孩子們,時而至家人的攤位跑跳,時而至我坐落於市場內的家中玩耍,絕大部分的童年都是在這個公私參半的場域中度過。
隨著年紀增長,其他同為市場二代的孩子們,漸漸迎向屬於「市場囡仔」的角色期待,不僅步入了工作崗位,也步入了各種才藝與學科補習班,乘載著各自父母的寄望,試圖在藍領的洪流當中,創造階級流動的機會;而相形之下,我則受惠於父母給予我的自由,我不但逃過了遊樂場與工作場域之間的轉變,也倖免於某種新時代下,對於孩子學業與才藝並就的追求。
然而,在這個公私參半的場域當中,市場不只是工作場所,同時也隱隱約約地拓展為張揚各家孩童的複合式舞臺。因此在走向「成年」的過程中,看見其他市場二代盡忠職守的同時,彼此共享的市場二代身分就猶如纏綿不絕的低語,總時時刻刻地凝視著某種我未完成的「責任」。
至於同處市場的父母,他們對我並非毫無要求與期待,只是相較之下,他們願意給予孩子相對高的自由與包容,可在某些重要的時刻,例如年節期間,我仍然需要背負起一定的「責任」,即便平時缺席的市場二代在工作上能給予的幫助不高,但我們都明白,有時「拋頭露面」的意義,絕對大於實質上的勞力付出。
升學上的教育衝突,看見彼此對於家庭親密關係的不同想像
2017年9月,我升上高一,連帶長年背負升學主義的壓迫與不滿,我在入學第5天決心逃離體罰成性的教育體制,選擇退學,並因緣際會地走向體制外教育,成為自學生,展開了將近4年的自學生活。可這段既不是在學校學習,也不是在市場作工的日子,觸發了母親的焦慮。
對我而言,學習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是基於個人心之所向而選擇的行動,因此我離開學校;可對於母親而言,她與大部分臺灣人的生命經驗一樣,皆是先由家庭走入學校,再由學校步入職場,「自學」的概念未曾出現在她的生命當中。又由於母親不擅中文,難以理解體制外教育的制度與資訊,更遑論理解其背後的理念。於是,資訊的不對等加上生命經驗的落差,便形成我與母親之間難以言盡的教育衝突。
2020年末,我與母親之間的關係愈發緊張,尤其在母親得知我有意透過特殊選才進入大學後,更是三天兩頭地訴說著她對大學的甜蜜想像,以及我能透過大學成為老師或律師所迎向的美好未來。在母親的言談間,我看見了她對於翻轉藍領階級的寄望,以及藉由讓孩子進入大學,覓尋一個屬於菲律賓母親的成功證明。而這份日以繼夜並以愛為名的期盼,以及這張母親為我規劃好的白領人生藍圖,卻再再地讓我抗拒這份過度親密而且過度干涉的親子關係。猶記得聖誕節那晚,母親若有所思地躺在床上,隨後語重心長的那句:「你上大學才有畢業證書,才能像姊姊一樣戴學士帽拍畢業照。」
關於這份期盼,我開始思索母親在菲律賓生活28年的人生。在菲式大家庭文化中,極其緊密的家庭共同體關係是母親生命的基底,她繼承著宗教、歷史與政經環境層層堆疊的民族性,也歷經一切離鄉背井、跨國移動而後生的苦悶與希望,從一位菲律賓女兒轉變為菲律賓媽媽,隨後轉變為菲律賓移工,再轉變為臺灣的新住民,走入第二段婚姻家庭。這之間的身分轉換,以及生命經驗的不斷交疊融合,無一不影響母親對於家庭親密關係的想像與期待。我日漸明白「與穿著學士服的孩子合照」不僅是母親的夢想,那更是一種對於過去生命總和的交付,尤其那是對於一位在親子關係中「缺席的母親」的合格證明。
或許吧,我能理解母親的期待,可我仍然害怕將孩子成就與母親榮耀牽連一體的親密關係。在升學的那段日子裡,每當母親再次將大學作為必然成功的生命框架,而向我訴說著過度夢幻而不可及的未來,我們總是因為彼此之間難以三言兩語道盡的生命經驗而身心俱疲。直到最後,縱使我的升學選擇剛好符合了母親的盼望,可我還是本能性地在放榜那天,隱瞞我錄取大學的事實。
放榜的對談,我與母親之間難以言喻的默契
2020年12月某日的早晨,我查閱其中一間中部大學的榜單,看見了自己的名字,可由於隔天仍有其他大學的面試,我仍打算準備過夜的行李,提前移動至外縣市。
其實關於升學,我也同樣焦慮。放榜當天的午後,我還是忍不住告訴母親我被大學錄取的消息,可在母親激動地問我是哪間大學時,我才連忙打住,並以玩笑的名義搪塞母親,便趕去收拾行李。
準備出發前,母親睜著眼兀自在床上發呆,即便我心裡有底,但還是試探性的開了口(為方便理解,以下對話翻譯成中文):
「你在做什麼?」
「我很擔心。」
「擔心什麼?」
「擔心你不去上大學!你告訴我實話!你剛剛說那間大學叫什麼?」
「沒有,我開玩笑的,我沒有上大學,而且沒有上大學又沒有關係。」
「有!你沒有未來,你沒有工作。我死了你怎麼辦?我非常擔心你。」
「我會工作養活自己啊,像之前我去早餐店工作那樣。」
「早餐店沒有未來。你不上大學就沒有未來。」
我與母親沉默了片刻,接著她卻突然開著玩笑說:
「你找個有錢的女生結婚好了啦,哈哈。」
「我不會跟女生結婚。」
「哈哈,你不會跟女生結婚,你要跟誰結婚?男生嗎?」
「對。」
「哦……哈哈哈!違反規則。」
不知為何,那晚我與母親的對話有別於以往的氛圍,算不上溫馨,也稱不上疏離。或許是母親意會到我升學了,也或許是母親對於爭執感到疲乏,而我在那耐人尋味的玩笑中感受到,某種原本屹立不搖於彼此之間的結好像開始鬆動,在似笑非笑的對話當中,我們彷若理解了什麼,又不完全理解著什麼。
進入大學,身為市二代與新二代的後續
最終,我選擇離開家鄉,進入了一所南部的大學,我與母親的教育衝突因而暫緩,原先與家庭之間過度交織的親密關係,也因為這段物理上的距離,漸趨和諧。而當我踏入「頂尖大學」的消息流轉於市場,市場於我的疆界也漸漸淡去,我不及其他兒時玩伴吃苦耐勞的童年不但既往不究,甚至轉換為某種光輝而四散,市場彷彿再度擁抱了我。
我明白,無論是我與母親的衝突,抑或市場對於二代的期待,「進入大學」僅是一種粗淺的手段,未來仍需要大量的溝通與互相理解。可在我離開原本的環境,而自身與他人之間不再是親密疊合的狀態後,我逐漸發現自身更願意試圖完成無傷大雅的「他人的寄望」。
我想,當人們將焦點放在自己欲求所見的事物,當他們能夠因此活得開心快樂,那麼,我與生俱來的「福氣」,是否就不顯得那麼突兀?而那些寄託於角色上的期待,也或許正因此而減少著,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