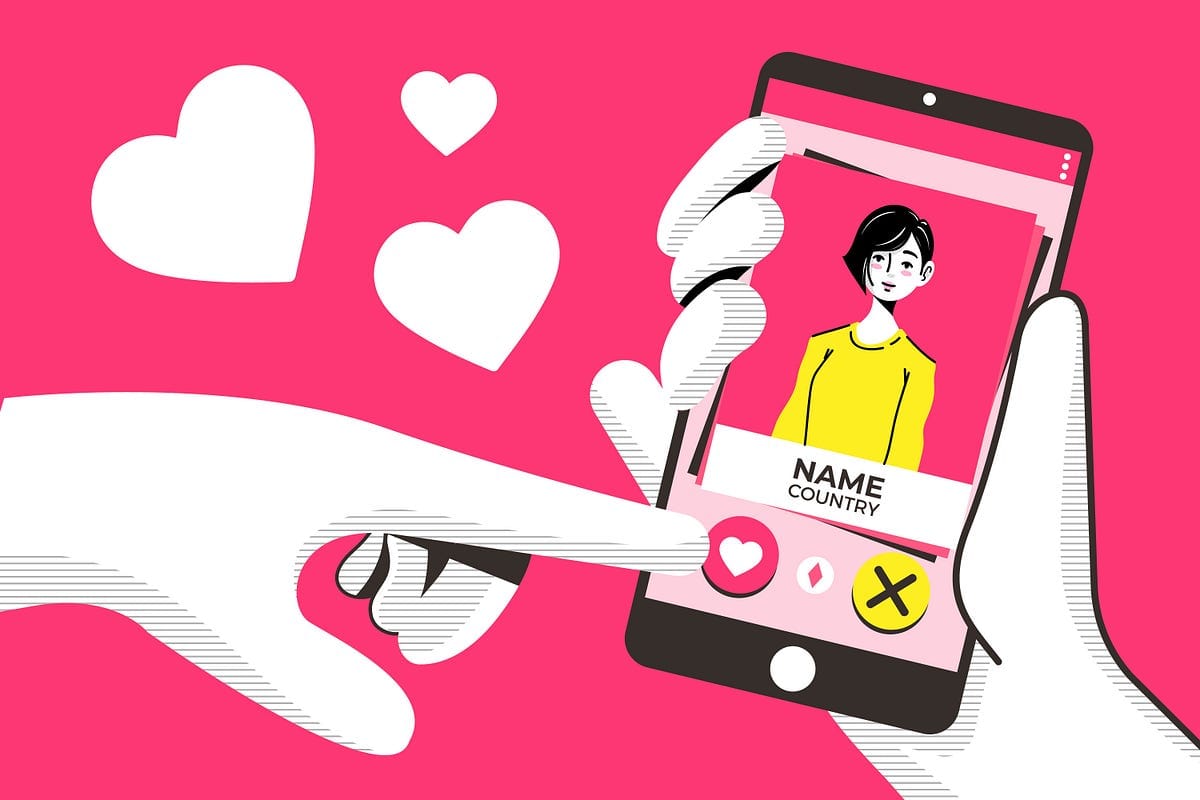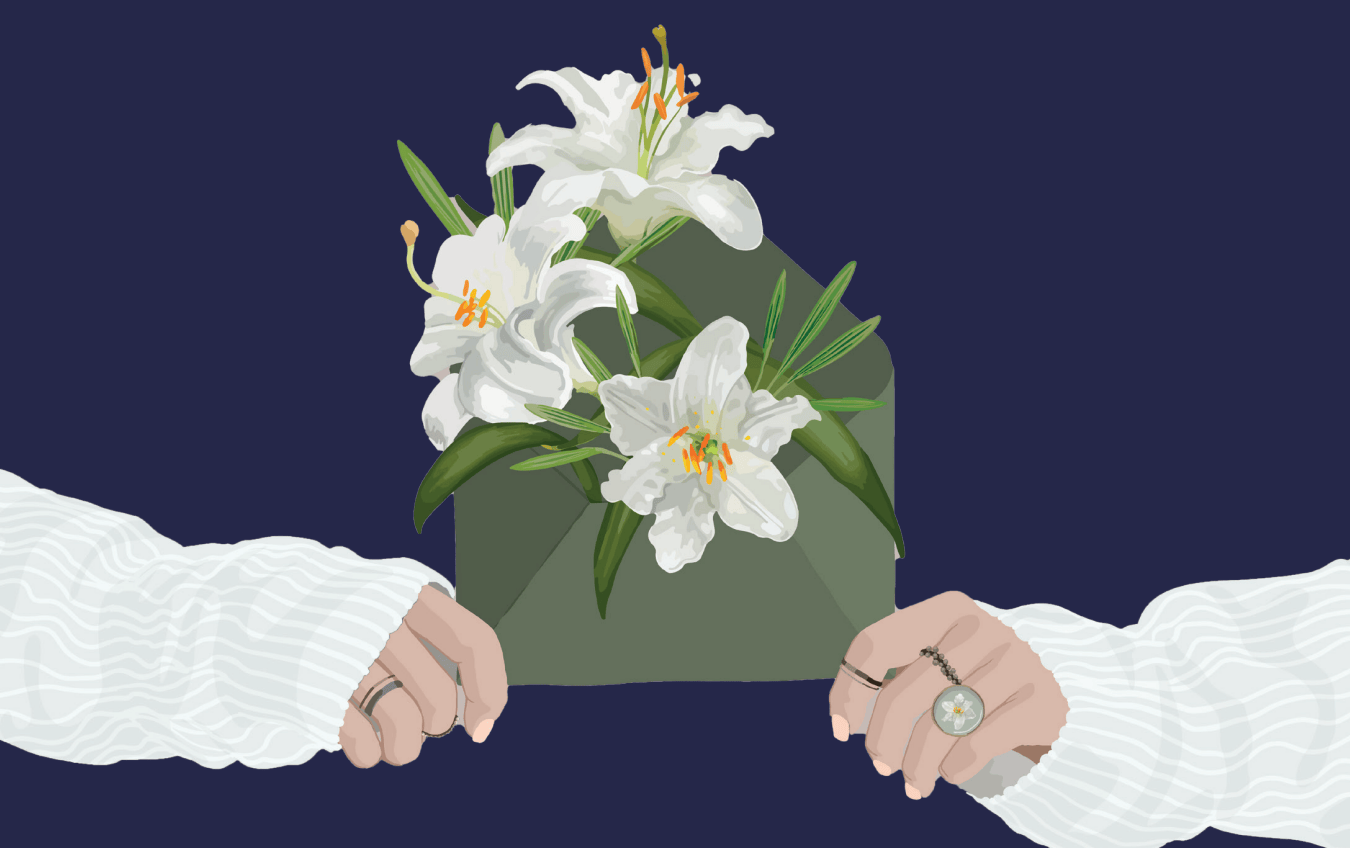專題企劃 / 白色恐怖的性別面面觀
施又熙 * /作家
*施又熙,出生於高雄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庭,為1960年代政治受難者第二代。作家。以白色恐怖為背景的創作出版包含:《月蝕》(2005)、《臺灣查某人的純情曲——陳麗珠回憶錄》(2008)、《向著光飛去》(2017)、《光的闇影》(2020)等。
如果歷史是一條長長的河流,那麼,我在哪裡呢?
如果白色恐怖的真相是一幅拼圖,那麼,拼圖裡有我的位置嗎?
臺灣走過了43年、幾乎是世界上最漫長的戒嚴時期,在言論與思想自由即生死存亡的箝制下,噤聲成為我們的桎梏。儘管白色恐怖在1992年「停止」,至今已逾30年,但噤聲的桎梏卻未全面解除。從一開始的政治受難者閉口不言,在政黨輪替後,國家開始投注關懷在戒嚴時期所發生的白色恐怖,許多專家學者從個人關懷記錄故事,轉而公開地大量進行口述歷史工程,政治受難者終於可以開口說話了,但仍然有許多受難者基於各種因素或創傷反應,不願意或不能開口敘說自己的故事。
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發現家屬是失語的,女性家屬多是不被提供話語權,在書寫白色恐怖歷史中是被隱而不談的,即便在眾多的口述歷史中,家屬/女性家屬的敘說往往也在補足受難者缺漏的篇章,或是更容易被提及與強調女性配偶如何在丈夫被捕後的守貞與如何地含辛茹苦養育孩子,缺乏家屬的主體性敘事。倘若白色恐怖的真相是一幅拼圖,那麼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受難者的聲音,我們也需要家屬的聲音,甚至,我們還需要執行者的聲音,唯有如此,真相才能更趨近於真相。礙於篇幅,在本文中,我想專注在女性家屬的故事,或者可以說是我的故事、我所聽過的女性家屬的故事,與我們的人生。
家屬的聲音之所以重要,並不在於他們可以補足受難者離家之後的缺漏篇章,而在於家屬被「留下來」之後如何面對當年不友善的社會環境。我的父親因為臺獨案件前後坐牢兩次,而我是在父親第一次坐牢時保外就醫跟母親偷生的孩子,換言之,在我出生前後,父親都不在家。父親二字對我而言像是一層難以穿越的迷霧,是個形容詞,從來都不是名詞。作為一名政治犯的女兒,一直都覺得自己是座孤島,因為在被「留下來」的家庭中,母親與長我9歲的姊姊常常相對垂淚,於是我只能孤單地成長,習慣性地自己吸收所有的一切。
童年對我而言,幾近空白,並不是沒有發生事情,而是我無法記住那些事情,極少數記得的畫面跟場景也常常會自疑那些事情真的發生過嗎?
那些還記得的,最早的記憶來自5歲的某個傍晚,母親騎車出門去喝喜酒,不久又返家,因為覺得有點莫名的忐忑,便帶著我跟姊姊一起赴宴。一家三口喝完喜酒返家時已晚,一到透天厝的家門口就立即發現家裡的玻璃門後面卡著姊姊的單車,顯而易見的,我家又遭小偷了。那個年代,政治犯家裡常遭小偷,根據大家的推測,多半都是情治人員偽裝行竊,想要翻找這些政治犯的家裡有沒有其他犯罪證據。而那個晚上也是如此。警察很快便抵達,檢查完整間透天厝之後,確認家中安全便收隊了。待我們回到樓上,發現家裡被翻箱倒櫃極為凌亂,但是那些值錢財物卻一樣不少。母親斷言又是特務來過了,既然沒有少財物,大家也累了,不如就早點洗澡睡覺,隔天再整理。等我洗完澡回到房間準備睡覺,掀開棉被卻赫然發現我的床上躺著一把菜刀。
沒有人知道如果那天母親沒有返家回來帶上我與姊姊,那把菜刀會在哪裡?會發生什麼事情?這些沒有發生的如果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這把菜刀卻對我產生了一生的影響。
長久以來,我總是無法安心地獨居,當我居住的處所超過一房一廳,睡在臥室裡總是擔心客廳會有人闖進來,所以我總要鎖門睡覺,並且在客廳留燈,躺在床上也要凝視著門縫,仔細地注意外面有沒有人影,直到累極入睡為止,因此我常態性地有睡眠障礙。甚至到了高中,那時已搬遷到社區大樓,如果母姊傍晚外出,我就會緊繃地鎖上所有的門窗,開亮家裡所有的燈,拿著我的網球拍坐在客廳,仔細地聽著所有的聲音,如果發現有異樣的聲響,便會握緊我的球拍去檢查再檢查。等母親回來,因為我鎖上所有的安全鎖,她們必須要按電鈴等我開門,我得飛快地把球拍丟回房間,開窗關燈開門,母親總說為何我每次開門都要這麼久,因為她從不知道我有這樣的恐懼與障礙。
時至小學5年級,那是美麗島事件剛發生過不久,父親正在逃亡中。某日放學的降旗典禮上,訓導主任站在升旗臺上極其興奮地告訴大家:「今天,那個江洋大盜○○○已經被抓了!」全校上千位同學又跳又叫地進入一種集體歡騰的奇幻狀態,彷彿那天是過年,發生了足以讓大家歡天喜地的事情。全校只有我們班上靜默無語,幾位同學偷偷回頭看我,因為他們知道我的父親是誰。數日後,我因為上學遲到,被訓導主任叫上升旗臺,他拿著麥克風告訴大家,「這個人叫○○○,她念○年○班,她就是江洋大盜○○○的女兒。」那一瞬間我幾乎進入了解離的狀態,更像是被囚禁在玻璃魚缸裡面的一條魚,看得見玻璃缸外那些人激動的表情動作,卻一點聲音也聽不見。在那種狀態下,其實難以判斷時間的長短,只知道下一刻當我再聽到聲音,是訓導主任以極其厭惡的表情推了我一把,斥我:「下去!」自此,展開我與其他班男生打架的歲月直至畢業,每天每天,在校園裡總會遇到其他班的男生以髒話罵我或是推我、扯我衣服,直斥要我轉學,因為我是學校的恥辱。
只有我們班上的同學對我是平和的,因為導師曾經跟同學們說過:「○○○的父親沒有做錯什麼事情,你們不要對她不好。」這也是我極年輕的時候就對心理學產生高度興趣的緣故,我很好奇,為何人會如此不同?為什麼導師要冒著被檢舉的風險也要保護我,可是訓導主任卻要這樣置我於險境?這是為人師表應該要做的事情嗎?升旗臺上被公審的經驗對我產生了「局外人」的影響,我總是在情緒上跟人群很疏離,也許我可以在跟人相處時表現得很親和,甚至可以讓大家很愉快,但是當大家開心大笑時,我卻完全不覺得那個笑聲跟我有關,那個快樂是我可以參與的,我與他人之間總是隔著一層清澈卻厚重的玻璃,一如11歲那年站在臺上的那一刻。這些事情我不曾告訴我的母親,因為我不知道就算她曉得了又如何?
就這樣如孤島般的成長,因為相信這個世界上只有自己能幫助自己,沒有他人可以依靠。甚至,也常常懷疑,自己真的曾經在小學5年級的時候被叫上升旗臺公審嗎?直至36歲重返文壇,因為出版小說上電視節目宣傳時,現場有人提到5年級這件事,我很震驚有人知道,也不諱言地直接在節目上提到自己常常懷疑這件事是真的嗎?數日後,製作單位打電話告知一位老師自稱姓○,是我的導師,他去電節目告知升旗臺那件事是真的。因為那通電話,我才確認了,原來那件事是真的。可是,距離那通電話已經又過了10數年,如今我常常懷疑的是,真的有那通電話嗎?
自疑與貶抑,成為一種生命的底色。
不管是難以獨居、局外人感受或是那些永不停止的懷疑,這些都是自然的創傷反應。近年來,臺灣在推動轉型正義工程中,也開啟了面對「政治暴力創傷」的大門,這是一個大家都極為陌生的名詞,卻是無法迴避的議題 — — 政治受難者在被捕、受刑與服刑的過程中承受了創傷,但是被留在社會的中的家屬,如我,如其他我所認識的二代姊妹們、男性們也同樣承擔了不同的創傷,而我們卻往往不知道那就是創傷。誠如我知道11歲那年在升旗臺上,我必然得要解離,這樣我才活得下去,因為大腦知道必須要這樣保護我,但我仍然不可避免也無法擺脫這一生都是局外人的情緒疏離議題。
我自然不會是在那樣的年代中唯一一個被叫上升旗臺去的家屬,只是我有機會成為一個作家,成為一個說白色故事的講者,較他人幸運地有了一些話語權,因此大家可以聽見我的故事,藉由這樣小故事的分享,試著讓大家去理解那個年代的社會如何看待政治犯及其家屬。但是還有更多無法言說的,甚至是被忽略與不曾理解的創傷,並不會因為白色恐怖的結束便停止反應。事實上,政治暴力創傷或說僅僅是創傷,至今都還是進行式。
這樣的創傷反應不只反應在生活中,極可能也反應在感情議題上。2017年我出版了《向著光飛去》,以4個如我一般的政治受難者第2代女性的感情故事來包裹白色恐怖,藉由這套小說我想要說的是白色恐怖的影響無遠弗屆,那些你以為完全不相關的人可能也是受害者。那些你所不知道的,一些小小的、古怪的生活習慣跟態度可能就是因為白色恐怖所遺留下來的後遺症。值得觀察的是,當書出版之後,我接到兩極化的反應,一些在俗世中的友人紛紛跟我分享,她們也曾遇到如書中男主角般的交往對象,是如何的溫柔體貼與穩重云云。與此同時,我也接收到幾位如我一般身分的受難者二代女性姊妹的回應,憤慨表示為何要寫愛情故事?表示怎麼可能會有像男主角這樣的人?甚至直斥我太過浪漫的也有之。當我接到那樣的斥責時,我的反應不是憤怒,而是一種心疼與哀傷,因為我們之中有太多人都不相信愛也不敢愛了,而愛,原本是每個人都需要的,真的有人完全不需要「愛」嗎?
葉光輝等(2006)以父親長期缺席狀態下的華人女兒們進行研究發現,包含父親以離異、死亡、囚禁、失蹤,甚至是以忽略的相處方式缺席的女兒們,常常會引發一種渴望父愛的情結。因為人生中第一位重要異性的缺席,導致女兒們與男人相處上的困境,甚至在缺席狀態下會自疑自己是不值得被愛的,更容易以低自尊、低自我價值的自我認同感詮釋自身,由此,在感情上往往是陷入顛撲困境的。於我,也曾是如此的。我們在面對適合自己的對象時多半是退卻的,在相熟的第2代姊妹中也不乏相似的案例,獨身、離異者大有人在。一位親近的姊妹是頗具才華的藝術家,高中時,其父在她面前被情治人員逮捕,此去直到該姊妹研究所畢業後才服刑完畢出獄,姊妹的青春歲月,父親都無法參與。而這位藝術家結婚、離婚,之後每每談戀愛都是小她非常多的年輕男子,每回我們見面都換對象,她也不明白為何總會覺得在某個時刻,就會想要跟對方分手,難道是因為這位姊妹花心嗎?
某日,在一個講座結束之後,跟姊妹談起此事。雖說年齡不該是問題,但或許是因為她的人生在父親被抓走的那一刻便停止前進了,潛意識裡總還覺得自己是高中生吧,總會尋找著極其年輕的對象,卻又不相信自己是值得被長久好好對待的,因為那個應該要在自己青春歲月時像座山存在的父親不見了。即便知道那不是父親自願的,但那種被拋棄的痛感如影隨形,甚至早已在自己不經意間縷刻入了骨髓,於是,總要在被人拋棄前便先主動拋棄了對方。
儘管這樣的現象並不必然一定要跟白色恐怖相關,但是加入了國家暴力的元素以及如我童年般的社會氛圍後,父親缺席下的女兒們在感情上遭逢困頓的複雜性,的確較之一般單純的父親缺席等因素要來得更難以處理及面對。缺席的父親如果日後回來了,其對待家人女兒的態度是重要關鍵。然而,許多的受難者長輩自己滿身的創傷,自救尚且無力,遑論以充滿愛的形式來彌補與家人女兒間的斷裂。尤有甚者,長輩自身的創傷已然造成重大傷害,家庭內部的氛圍也隨之傾頹。面對返家的陌生父親,女兒們往往也處於不知所措的相處窘境,一方面渴望父愛,另一方面又疼惜受創的父親;自己不忍苛責父親的缺席及無法彌補,卻又無力修復自己內在的渴望與傷痛。隨著時間的積累,那許多的痛與渴望成為了家裡不能說的禁忌。抑或是少數受難者在出獄後,權力冠冕加身,形成一方大老,家人及女兒們或也陷入了另一種噤聲的壓力之中。
儘管白色恐怖已經過去了,但是我們知道創傷具有代間傳遞的巨大傷害力,滿身創傷的第1代與第2代,無力提供自己安全感的人生,便也常常難以持平而中庸地傳遞愛給下一代。如此,帶著困擾的第3代又該如何去詮釋自己的家族,與自己被對待的方式?如果在缺乏安全感與愛的環境中成長,又該怎樣去發現這一切的起源與改變的可能?
本文的最後,我想要提醒的是,儘管政治暴力創傷是真實存在的,但這並不是所有受難家庭處境的唯一解答。有些受難家庭在缺席者返家後,幸福而美好地前進著,有些受難家庭則支離破碎。這些差異終究要回到一個人的本質來理解,政治暴力只是一種加成的效果,並不是全部的答案。如果把一切的好壞全都歸納到政治暴力創傷,似乎也太輕易了。因為我們都生活在這個世俗間,我們總是有許多困難選擇要面對,有時候是社會環境,有時候是家庭壓力,有時候是因為自己的良善跟自己的選擇。一如即便在書寫的此刻,我仍然要斟酌著可以敘說的故事以及禁忌、性別平等或是普世價值,然而在國家暴力的故事中,卻仍然有著難以跨越的界線。這條界線的衝破尚有賴於全體社會的提升,以及願意更客觀而非以儒家倫理中心為準則的看待世間事。
歷史的長河裡總是關注那些最鮮明而顯要的,許多被忽略的聲音彷彿泡沫般消逝。唯有所有的聲音都盡力被撿拾了,真相才能趨近於真相。但願我們都能開始關注那些被隱去的聲音,但願我們都能開始傾聽。

參考文獻
葉光輝、林延叡、王維敏、林倩如(2006)。父女關係與渴望父愛情結。教育與心理研究,29(1),93–119。